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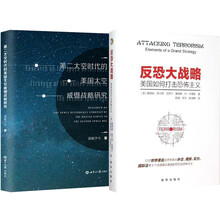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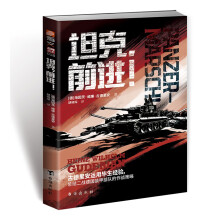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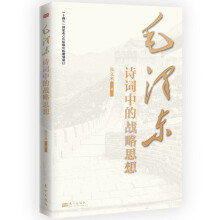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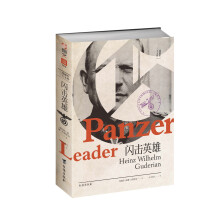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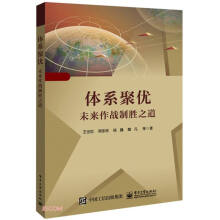

《最残酷的夏天》是美国战争文学大师、普利策奖得主菲利普?卡普托的倾力巨著,历时9年精心打磨,畅销欧美30年,中文全译本隆重上市。
亲历越南战争的菲利普·卡普托中尉,在越南的湿热的雨林中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无情,见证了战友间的手足情深,见证了人性的矛盾挣扎。卡普托诠释了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战争对人的影响,被称为“卡普托方式”。
《最残酷的夏天》首度全面揭秘了越战真相,更有百张战地图片曝光。在文学中读懂战争,在战争中寻找硬汉,在硬汉中发现自我。感受最真实的越南战争,品味最经典的战争文学,尽在《最残酷的夏天》。
你曾耳闻战争的惨绝人寰,却未见证战场背后的真相。
令人不寒而栗的雨林、令人惊恐的未知、令人绝望的等待。
身处最残酷的战争,你!何去何从?
此情此景,时间停滞,艺术消失,音信全无,社交成空。然而最糟糕的是,惨死的恐惧和危险挥之不去,人之生活,孤苦无依,落后贫瘠,歹毒罪恶,野蛮残暴,生命短暂。
——霍布斯(Hobbes)《利维坦(Leviathan)》
十月下旬,敌军一个营袭击了我方一个直升机基地,导致基地守卫人员50人伤亡,摧毁或破坏飞机达40架。两天之后,另一支北越军营袭击A连80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值守的前哨,我方死亡人数22人,受伤人数超过50人。每天都有人因为埋伏和陷阱或死或伤,救援直升机顶着漫天风雨在低矮的空中来回飞行。
此时,团部的心情开始和天气相得益彰了。不过这时候离战争最末几年,全美军队上上下下失落沮丧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不过此刻我们的心理状态较之于八个月以前的趾高气扬,已经是十万八千里了。大家冷嘲热讽,听天由命,郁郁寡欢。从部队里那些黑色笑话中就可见一斑,“嘿,比尔,你今天要去巡逻。要是你腿被炸掉了,可以把靴子送给我吗?”也可以从我们唱的歌词中管中窥豹。有些哀伤凄凉的西部乡村曲子如《底特律城(Detroit City)》,副歌部分充分表达了每一位步兵的心之向往: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噢,我想回家
有些歌曲则充满了黑色幽默。例如《一肚子战争(A Belly-full of War)》,这是A连一位军官编的行军歌。
噢,他们先教我杀人,
然后强留我在山里,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天气不是风就是雨,
我脑袋全成了糨糊,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噢,天上太阳毒又热,
还一脚掉进雨林坑,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如今我疲惫又害怕,
想留条小命见父老,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你在河内挺胸阔步,
早忘了我这小可怜,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我张着小嘴倒在地,
五脏六腑另寻下家,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战争还有另一面,没有歌曲、也没有笑话去讥讽。战斗不仅愈发激烈,也更为险恶。我们和北越军都已经习惯残暴冷血。第一营的一位无线电员被敌军巡逻队抓到了,捆起手脚用棍棒击打,最后一枪打死。他被抓三天之后,我们在翠峦河河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手脚依然被绳子捆绑着,后脑门上有子弹穿过的洞。另一团的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捕,后来在一个坑里发现了尸首,他们也被绑着,头颅被凶手的子弹打爆。一位名叫亚当·辛普森(Adam Simpson)的黑人军官——匡蒂科的校友,带领的一支28人巡逻队遭遇了埋伏,敌方北越军共有200人,这支巡逻队几乎全军覆没。如果北越军不至于连伤者也赶尽杀绝,恐怕还能多几个生还者。北越军从埋伏中跳出来,冲向倒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只要看到有生还迹象,立即开枪打死,我那位校友没能逃过一劫。最后死里逃生的两位队员是躲在已经牺牲的队友尸体下面装死,由此才虎口脱险。
我们以牙还牙,有时是出于功利意图。大家众所周知,被俘虏的北越军能活着走到战犯营的少之又少,上报的消息一般是“试图逃跑故开枪射死”。有些连队都懒得去逮捕战俘,只要看到北越军就取其性命,有些越南人只不过是嫌疑人也难逃厄运。后者一般都算作已死敌军,因为有不成文规矩——“如果对方死了,又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
在战争中,一切事物都快速变质腐烂:尸体、皮靴、帆布、金属和道德。或烈日骄阳,或风吹雨打,我们在陌生的沼泽地和雨林之中战斗,人性渐渐不见踪影,就像步枪枪管里的防护粉消耗殆尽。我们的战斗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冲突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杀戮。这不是欧洲那些规规矩矩的作战,而是在无规矩无法治的蛮夷荒野之地,为了自我生存而互相残杀。这场战斗,是战士为了保住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性命。出于这份个人情感,他们不在乎杀了谁、杀多少、怎么杀。有些人批判其残暴之举藐视文明战争应有之金科玉律,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战场伦理准则企图为原本就没有人性的战争盖上人性的遮羞布。依照那些“交战条例”,如果朝正在奔跑的越南人开枪,符合道德规范;但如果朝站立或行走的越南人开枪,就有违道德伦理。如果近距离射杀敌军战俘,不合规矩;如果狙击手远距离射杀除了被捕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敌军士兵,则合情合理。步兵用白磷手榴弹炸毁村庄,于法不容;可如果战斗机飞行员朝村子扔汽油弹,则无甚不妥。伦理成了距离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用先进武器远距离杀人,绝对不会违背伦理。而且华莱士·格林尼将军颁布的令人血脉贲张的命令:干掉北越军。在那个爱国主义高涨的肯尼迪时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可以为祖国母亲做些什么?”祖国母亲回答:“干掉北越军。”这就是策略,这就是我国部队高层精英能构建出的最佳策略:有组织屠杀。不管有无组织,屠杀就是屠杀,因此,谁还去说什么规矩伦理,而且这场战争原本就没有规矩伦理。
十一月中旬,我主动提出要求,于是转到第一营的一个连队。我对战争的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虽然没有不切实际的梦,不过还是主动要求加入连队。原因不一而足,最首要的是枯燥乏味。除了记录伤亡人数,我实在无所事事。我觉得一无是处,其他人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我却待在后方毫发无损,心中着实羞愧难当。我不否认,前线仍旧对我很有吸引力。不论战争是对是错,战斗总有一种磁力。战火之下,似乎能活得更有滋有味,脑袋更灵敏锐光,思维更清晰敏捷。也许还有一种反作用的力量,心驰神往中夹杂着排斥厌恶,希望期盼之中又有些失魂落魄。你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情绪崩溃的边缘,那种晕头转向不是喝杯酒或嗑粒药就能匹敌的。
另一动机是怕自己会精神失常。那天在食堂,我精神恍惚看到莫拉和哈里森被死神上身,这已经成了青天白日、时时刻刻揪住我不放的噩梦。我眼前出现的任何人,眼帘之中都会浮现出他们的死尸模样,包括我自己。我还看到自己的尸体,甚至有时我不仅看到自己的死尸,旁边还有围观者。我看到,没有我的地球继续旋转。每晚入睡前,自己即将一命呜呼的不祥预感便向我袭来。有些时候我也会暗自发笑,要是自己都能看见自己死后的尊容,估计也不会把自己当人看了,而且如果还能看到他人死去的样子,也就不会把别人当回事。上帝或大自然开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玩笑,我们一个个全是受害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尸体会面带笑容。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们听懂了笑话。有些时候,我也哑然失笑,可绝大多数时候压根儿不好笑,我敢断定,再多数几个月尸体,我恐怕就要去精神病院了。在文职队伍里,有太多闲暇时间对尸体念念不忘,在连队里估计就没这闲心了。这是在战争中保住心理健康的秘方——不去想。
最后的动机、仇恨,埋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时自己都没意识到其存在与否。可我现在认识到了,虽然承认这一点让人心痛。我内心燃烧着对北越军的仇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屏着一口气,不言而喻:复仇的欲望。我不是因为敌军的政治路线而对其恨之入骨,而是因为他们杀死了辛普森,这些杀人凶手把这年轻人的尸体扔到河里,还因为他们炸死了瓦尔特·列维。报复是我主动要求加入连队的另一原因,我希望伺机干掉凶手。
我在冲绳的老室友吉姆·库尼(Jim Cooney)从第三营调来接替我。我给他的伤亡文档比我六月份接手这份工作时厚了好几倍,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卡扎马拉克(Kazmarack)开车送我离开1-1部队总部,哈密尔顿(Hamilton)中士为我送行。我一定会想念他的,多亏了他的幽默风趣,过去五个月里我好歹还能在旁人面前保持一副大脑清醒的形象。哈密尔顿经常肠胃不好,他火急火燎抢在上校的前面去厕所,遭人大声斥责,他反驳道:“上帝啊,长官,我被胡志明报复了。我能怎么办呢,就因为我的便便上面没有上校雄鹰标志,我就要认命拉在裤子里吗?长官,大便和死亡是不认军衔的。”
营地总部到处是泥水,在法国要塞附近搭建了一簇帐篷和掩蔽壕。我开始“奔赴刑场”了:到副官帐篷递交任命书待签字,到营地救护站交体检表,回到副官帐篷把调职书收入个人服役档案,然后去见指挥官——四肢瘦长的哈奇(Hatch)中校。他告诉我,我将加入C连的一个排,以前是瓦尔特·列维带队的。尼尔(Neal)上尉是总队长,迈克洛伊是执行军官——他的服役时间延长了。中校吩咐完工作,我回到副官帐篷等着查理连的司机把我接走。外面大雨滂沱,已经没日没夜下了两周了。
司机是一等兵华盛顿(Washington),他驾驶的那辆吉普车裹了厚厚的一身泥。华盛顿和所有连队的司机一样,活跃爱动,乐呵呵的,助人为乐。那些懒惰懈怠、臭脸一张、服务不周的司机就要扛把步枪,被发配到前线打战。吉普车穿过戴拉山口,由于没有挡风玻璃,所以雨水都打在我们脸上。路面早就变成了一条黄泥溪流,蜿蜒绕过一个个村落,这些村子因为牛粪和鱼露酱散发着阵阵恶臭。路两旁的一片片稻田和一排排香蕉树被水淹没了,香蕉树宽阔的叶子在雨里垂头丧气。华盛顿换挡加油,吉普车沿着一个平缓的山丘向上爬,车轮慢转,快到顶时吉普车摇摇晃晃。我从那儿能看到前方半英里处有一个T字形的交叉口,一簇茂盛的树林里面有一个村子,接着又是稻田和山丘,一座挨着一座,一直延绵到远处的黑色山岭。雨林树冠顶上笼罩着厚重的烟雾,也给那些山蒙上一层危机四伏、神秘莫测的面纱。我们开始下山,路软塌塌的,像是两英尺厚的红棕色布丁。有几位农夫站一个村子的水井边上,清洗他们的腿和脚。远处,一把机关枪正很有节奏地开火射击。华盛顿转到T字交叉口边上的一条岔路,路过一间水泥房子,墙壁上好多子弹弹片穿过的洞眼。房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81毫米迫击炮正在朝远处山丘发射。炮弹在山丘顶上形成一股灰色烟雾,山丘也是灰色的,像是雨里的矿渣。这条岔路旁边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峡谷,路尽头是一排低矮凌乱的山丘。C连的营地就在前方了。帐篷零落地搭建在一台105大炮周边,在群山、枪炮、泥泞和雨帘遮掩的山脉之中,其亮色条纹的瞄准标杆看着尤其喜庆,很不搭调。这条路连接营地和前哨,一群海军陆战队队员正步履维艰走在路上。他们排成一列,速度缓慢,耷拉着脑袋,身上那件长斗篷在风中扬起。斗篷上形成一个凸出的包,后背上的步枪藏在斗篷里面,枪口朝下,以防止雨水淋湿。队员们低着头弯着腰,像是一群驼背忏悔的和尚。
在总部帐篷里,尼尔上尉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瘦高结实,眼神冷漠,薄薄的嘴唇紧绷着,有点儿像描绘古代新英格兰课堂的素描画上的古板严厉校长。我把自己的任命书交给他。他从自己那堆文件中抬起头来,眼睛除了原本的浅蓝色,再没有别的情绪。
他说:“卡普塔中尉,早就想让你来了。”
“长官,我姓卡普托。”
“欢迎你。”他想挤个微笑,可没成功。
“卡普塔先生,我让你负责第二排吧,自从列维先生牺牲之后,他们一直没人领导。”
“长官,我在匡蒂科就认识列维先生了。”
“第三排和武装排也没有领导。”
他站起来,打开一张地图,向我说明局势。这个营,实际上整支队伍,都处于防守阶段。我们的任务是遏制北越军再度袭击飞机场,因此一定要守住主防线。现在没有制订任何反攻计划,小规模的分队或排巡逻除外,可即便他们的巡逻区域也控制在主防线两千米之内。
连队正前方从T字交叉口向南延伸,直到翠峦河,近一英里左右。这距离是一个完整连队能够守卫距离的三倍,而且这支连队人数不足。主防线缺口位置设置了大炮。连队按惯例设置安排任务:两个排——还不足够伏击巡逻队的人数,负责夜间防守主防线。第三排负责守住查理山,这个战斗前哨大约位于前方七百米处。清晨,防御线必须保证25%的守卫警戒,其他人则步行半英里回到营地吃顿热气腾腾的饭,护理枪支,休息养神。下午,他们去接替上午的执勤人员,在各点守卫,或是进行日间巡逻。晚上,依照惯例继续循环。
地雷和陷阱是造成这连队伤亡的最首要原因。有时也会遭遇狙击手,迫击炮则是极少数情况。我必须高度留意我们排的队员有没有患上足浸病。队员们总是湿漉漉的,而且总是体力不支,有些时候还饥肠辘辘,因为吃的东西都是C类配给品冷餐。但是,我绝不会让他们懈怠。他们一懈怠就会想家,想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能让步兵想家。明白吗?明白。有问题吗?没有。
“很好,卡普塔先生,你今晚就去防线,现在去拿装备。”
“长官,我姓卡普托,读成‘托’。”
“随便。你今晚去执勤。”
“遵命,长官。”我暗自想,这是我遇见过的最没幽默细胞的一个人。
……
点评《最残酷的夏天》
译者序
序 幕
绚烂的星火之战
死尸军官
死亡的灰色国度
落 幕
后 记
——约翰·格里格力·杜纳(John Gregory Dunne),《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头版)
★“这是我所撰写过的书评中最沉甸甸的一篇。我想告诉大家,《最残酷的夏天》是对我们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个人记载。的确如此,然而,你是否愿意开卷阅读?哦,我真希望自己能掌控你的生活,这一刻就好。如果你不读《最残酷的夏天》,我就扇你一个耳光,抢走你di一个孩子,冻结你的信用卡,什么我都干得出来。赶紧读!我现在已经病态般地迷恋上这本书了。”
——D.凯斯·马诺(D. Keith Mano),《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改变未来外交和军事走向的人们能将卡普托的这本书摆在床头。本书措辞严厉,言语坦诚,字字珠玑,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让人们理解了斗争的诱惑性。本书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本书寓意深远。”
——玛格丽特·曼宁(Margaret Manning),《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如果某人曾亲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龌龊,那他对战争的厌恶和憎恨往往令人信服,合情合理。但是,卡普托(Caputo)坚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包括他本人,战火硝烟和直面死亡所带来的情绪往往接近癫狂之喜,夹杂着疑惑与焦虑,这种说法同样令人深信不疑。战争如同强劲的毒品,自然能带来近乎超验之感。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在本书中用动人而又诚挚的笔墨描绘了恐惧与勇气,最真实地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我们永远相信,他是一位勇士,那场‘绚烂的星火之战’成了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梦魇,几乎将他淹没丧命,而在这之后,他依旧继续战斗。”
——威廉姆·斯特隆(William Styron),《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只有一名勇士才能写出《最残酷的夏天》;他是一位勇敢的斗士、诚实的男人、刚劲的作家。他的作品阴森惊悚,大获成功,将会流传yongjiu。”
——斯蒂芬·贝克(Stephen Becker),《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ews)》
★“每一场战争似乎都有人论述:在我看来,卡普托精准地指出了我们在越南战争中的所有损失。”
——C. D. B.布莱恩(C. D. B. Bryan),《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不为别的,就为其反战的精彩论述。本书精妙绝伦。”
——泰利·安德森(Terry Anderson),《丹佛邮报(Denver Post)》
★“在这本刚劲有力的著作中,卡普托完成了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必须完成的事:面对内心的敌人,熬过伤痛。”
——皮特·J.欧格尼本(Peter J. Ognibene),《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这些讯息是新闻记者无法提供给我们的,它们来自黑暗之心。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新闻周刊(News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