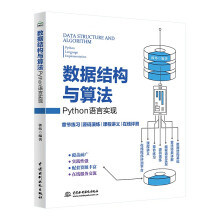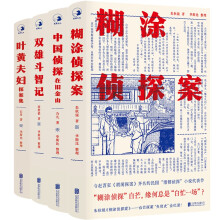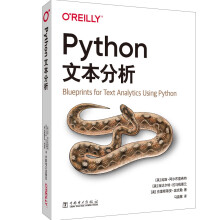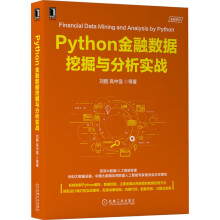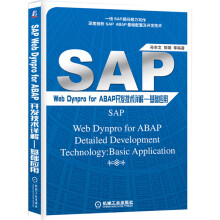“美丽的女士,你怀孕了吗?”当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那位党卫队讯问者面带微笑,双腿叉开站在她面前,像法医检验尸体那样对她上下打量。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站定在这位28岁的斯洛伐克女教师面前,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露天操场上,因为羞愧难当而瑟瑟发抖。就在几个小时前,她来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时间是1944年10月。
佩莉斯嘉还不到5英尺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些。她身旁站着大约500位裸体妇女,彼此几乎素不相识。她们都是犹太人,到达时惊恐不已。她们从欧洲各地的家园或隔离区被运到这座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她们每60人一组,被关在封闭的货运车厢内,每列火车长达55节。
车厢被打开那刻,她们大口喘着粗气,来到臭名昭著的铁路“站台”,置身于纳粹最有效率的灭绝系统正中央。这个灭绝系统被统称为奥斯维辛。她们马上被赶下车,叫骂声“滚出来!”或者“快滚,犹太猪!”此起彼伏。
在混乱与骚动中,人潮被面无表情、身穿肮脏条纹囚服的囚犯头目引导着,挤进坑坑洼洼的操场,而党卫队军官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用皮带牵着跃跃欲试的恶犬。根本没有时间寻找亲人,因为男人和女人很快就被分开,孩子们则被推入病人和老人的行列。
虚弱到无法站立的人,或者因为挤在闷罐车厢太久而四肢僵硬的人,则被枪管戳、被皮鞭抽。“我的孩子啊!我的宝贝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
在这长长的、被剥夺净尽的队伍前方,立着两栋低矮的红砖建筑物,每栋建筑物都带有巨大的烟囱,喷着黑色油烟,涌向铅色天空。灰色的浑浊空气夹杂着腐臭的、恶心的味道,直冲鼻孔,直灌喉咙。
在与朋友和家人分开后,年龄在10岁至50岁之间的年轻妇女,如入漏斗般通过一处电网环绕的狭窄通道,类似的电网还包围着这片巨大的营地。惊得不知所措的她们,步履蹒跚地走过那两座烟囱,走过几处深坑的边缘,走到一座巨大的单层门楼前面,那是隐藏在桦树林后面的浴室。
她们就这样不明就里地在集中营里“入住”,最初的步骤是被迫交出最后那点财物,被迫脱去所有衣服。她们用五花八门的语言大声抗议,却只是换来殴打和恫吓,迫使她们服从荷枪实弹的党卫队看守。
她们全身赤裸地穿过一处宽阔走廊,来到一个大房间,几乎所有这些母亲、女儿、妻子、姐妹都被粗暴地剃去全身毛发,动手的是男女囚犯,德国守卫则在旁边不怀好意地观赏着。
在被电动剃刀处理过后,她们几乎已无法辨认彼此。她们每5个人肩并肩走到点名区,在冰冷潮湿的烂泥地上赤脚等待超过一个小时,接受第二轮“筛选”。筛选者是一个男人,后来被人称为“死亡天使”。
门格勒医生,穿着严丝合缝、裁剪得体的灰绿色制服,佩着闪亮的臂章和银色骷髅领章,手里拿着一双袖口大得出奇的灰白山羊皮长手套。他的棕色头发用发蜡抹得一丝不苟,他随意地左右摆弄手套,在队伍前面来回踱步,审视着每一名新来的囚犯——每当遇到特定的对象——他就会问她们是否怀上了孩子。
轮到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时,她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决定如何回答这位面带笑容、门牙漏风的军官。她没有片刻犹豫。她果断摇头,并用熟练的德语回答道:“没有。”
当时她已怀孕两个月,她期待着为丈夫蒂博尔生下孩子(她希望蒂博尔就在这座集中营的某处)。她完全不知道,如果照实回答,到底会拯救自己,还是会把自己和孩子推向未知的命运。但是,她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她以一边手臂遮住乳房,另一边手臂盖住下体,祈求门格勒会相信她那生硬的否定回答。那位“慈眉善目”的党卫队军官迟疑片刻,凝视着这位年轻“可人儿”的脸,然后就径自走开了。
他又走过三位妇女面前,猛然抓住一位畏畏缩缩的妇女的乳房。几滴乳汁让这位妇女无所遁形,她怀孕至少十六周了。门格勒往左挥了挥手套,她就被拽出队列,被推到操场的角落里,跟那群战战兢兢的准妈妈挤在一起。
那些瞠目结舌的妇女当时还都不知道,一支队伍意味着生存,而另一支队伍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些当天被门格勒选中的妇女,对此一无所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