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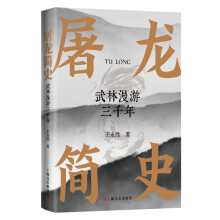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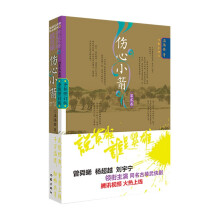
椴公依旧以他犀利精到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场关于文明建构的历史画卷。
自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发动政变,占据长安后,整个前秦处于风雨飘摇之势。长安城中,各股势力都变得有如脱缰的野马:有氐族豪强寻衅生事,有先帝苻生与强太后一系死而不僵,更有晋、代、凉、燕等外部势力虎视眈眈。而王猛为苻坚所规划的混六合于一炉的帝王大业,就在这乱局之中缓慢而艰难地展开着……
楔子
“她在升平元年出生。”
“在永兴初年遭遇兵祸。”
“然后,在光寿元年死了。”
女人静静地抬起眼,望着门口逆光处的那个男人,干涩地问:“先生,你说她一共活了几岁?”
升平、永兴、光寿……
男人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
一岁……
他望着那个女人,她身下破败的蒲席,与怀里空抱着一个襁褓。
那孩子活了还不到一岁。
女人浑身的衣衫破旧,只这襁褓上的锦绣如新。那襁褓死死地封着,什么都没露出来,包括那本该有的小脸儿、小手儿。可想象中的小手还是在那里痉挛着,抓着那女人的心肺,小脚还在那里蹬踏着,踩着那女人的肝肠。
女人的表情只是木木的,眼睛里只剩下空洞。
“一个多月了,我还没有埋她。”
“我不能轻易埋她。”
“因为她姓谢,是谢家的人。”
那个“谢”字出口时,仿佛有什么猛地标挺在她的眼前。
这一年是公元357年。
是晋的升平元年,燕的光寿一年。
同时,还是大秦的永兴元年。
仿佛单只割裂河山还不够似的,帝王们又重重地割切开了时间。
那一年,晋室的皇太后褚蒜子刚刚归政给年满十五岁的皇帝司马聃,改元升平;燕国的慕容隽携数十万铁骑南下至邺城,定年号光寿;而大秦的苻坚刚刚诛暴登基,建年永兴。
小茅屋内,一切时光仿佛都静止了,随着那女人的视线,凝结在襁褓之内。可就在这小茅屋外,几千尺的晴空下,划过那男人耳边的年号正破空而去,在几万里的河山上纵横激荡,往来呼啸……
锋棱过处,血流漂杵。
* * *
公元357年的人们应该不会想到后世会用什么纪元来标识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身边的纪元已整个儿的混乱了。他们怕是并不知道那些活跃在棘城之北、颛顼之墟一带的慕容鲜卑们,踏着清早的晨霜纵马驰猎时,生活在秦岭西侧、略阳之境的氐族人天还没有放亮;更不知道疏勒月氏一带的人们此时正自酣睡——不知道那亘古之日是轮流地唤醒着鲜卑、匈奴、汉、羯人、氐人、羌人与西域诸胡的。
他们怕只知道:不知怎么,这些东西遥隔、山长水远的诸族之间突然间就互相搅和在一起,开始彼此酣战了。
公元357年,后世所谓的中国境内的天下,正在不停地分裂、整合着。
北方来的鲜卑人的铁蹄已踏入邺城之地,且于此立国,国号“大燕”;汉人的朝廷衣冠南渡之后,终于在建康站住了脚,国号依然是“晋”;而西边略阳出来的氐人则在长安暂时扎下了根,立国号为“大秦”。更别提那些诸如“代”“凉”“仇池”等散落边荒的小国了。
而在野火未熄,干戈偶歇的难得的间隙,他们回头遥望,百五十余年前的那个“大汉”只怕如一块昏黄的、色若金盆的、巨大的完璧,遥遥地做为背景,映衬着这百五十年间的战乱。
没有人敢相信,还曾有一个“天只一日,人仅一君”的朝代曾屹立四百年,还曾把他们这些匈奴、鲜卑、羯、氐、羌人跟汉人们合拢在一起,并世耕猎、同乐蕃息。
让我们拍一拍那尘封在故史上的沙土,把这一段已沉没于史书中的故事,从那一年秋八月,一队自南阳向陇头迁徒的流民身上讲起吧……
楔子
第一章 麦子
第二章 宫城
第三章 板荡
第四章 谯楼
第五章 鬼方
第六章 宗室
第七章 长夜
第八章 早朝
第九章 烙印
第十章 家国
第十一章 郊祀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