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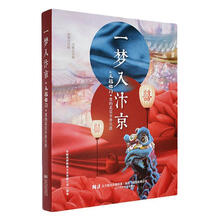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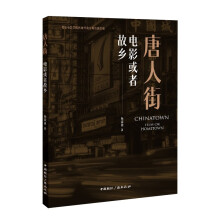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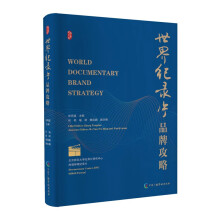



致中国读者
引言
导论
第一章解决问题的艺术
第二章那么,问题是什么?
第三章确定问题之所在
第四章处理问题
Part 1 一些常见问题
第五章废话滔滔
第六章恍惚、失落和困惑
第七章沉闷无味的本质
Part 2 有关情节的问题
第八章太多了,太快了
第九章太依赖解释
第十章缺了点什么
第十一章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在时间与动作之间架设桥梁
Part 3 有关人物的问题
第十二章什么是人物
第十三章回顾人生轨迹
第十四章沉闷、单薄和令人厌烦
第十五章主动变被动
第十六章闪回
Part 4 有关结构的问题
第十七章场景中的阻断
第十八章建置与完成
第十九章晚进早出
第二十章好,系好你的安全带
第二十一章结尾
第二十二章疑难解决指南
附录:中英文片名对照表(以英文字母为序)
“悉德书中揭示的剧本写作知识对我的影响就像水对巧克力的溶解作用,并促使我创作了《浓情巧克力》。以前困惑的问题现在茅塞顿开,过去阻滞的地方如今游刃有余。”
——劳拉·艾斯库威尔,《情迷巧克力》等影片的编剧
“如果我在写剧本……我会把悉德·菲尔德随身携带,随时参考。”
-——史蒂文·布奇柯,《纽约重案组》编剧、制片人、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