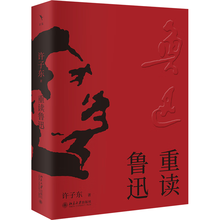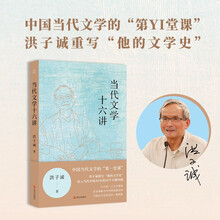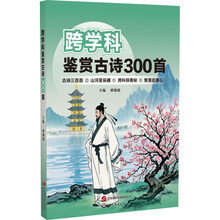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对现实的指涉,常常纠结于欲望实现与欲望挫折的轮回,在这种纠结的背后,隐喻着我们时代的“幸福生活”。“读报代替了早间祈祷”,这是黑格尔老人百多年前对他的时代的惆怅慨叹。消费时代的小说家们乐观地以为历史开始上行了,历史将从黑铁时代走出,然后迅疾地跨过青铜时代与白银时代,迎来天人关系与群己关系的黄金时代,少有人理会黑格尔这句魔咒。盘点一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无处不见粗鄙的欲望对人的鞭策与奴役,抑或人对日常生活的五条件投降!当下小说明显地呼应着这一事实。下面以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做一分析。
一、为什么超越经验的21S活值得一过?
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中心能指(主能指),除了“欲望”,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更准确合适的代用词。私己欲望代替了某种精神召唤成为叙事的驱动力;同样又是欲望腐蚀瓦解了任何超验水平上的生命目的,“目的”已陷落成为“盲目”。欲望宛若一只强悍而且肥胖的章鱼的吸盘,五条件地捕获了大家——或者倒不如说,是猎物急不可耐地扑向了捕猎者的爪网。
陈步森(农民工)、陈三木(假道学教授)、刘春红(妓女)、周玲(公司白领)甚至理想主义者李寂(副市长)、苏云起(公益事业召集者),在他们迷途的早年,统统无法逃脱欲望吸盘的魔力——消费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捕捉了他们,这种“被动性”是注定的,它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容”。他们疯狂地抢钱、勾引女学生、做假账、收受贿赂、盖豆腐渣楼……在欲望的金黄色光泽中,在“经獸超验”的二元搏斗中,他们的世俗理想乌托邦终究在消费时代的物质龙卷风面前一败涂地。
世俗性的解放是以回到“身体诉求”为主旨的,这一取向在樟坂的人们那里,是一个“硬道理”,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追求人身体的扩展与自足诉求,身体的冲动不断突破理念对身体感觉阀的限定,建构身体“造反”的逻各斯。
但北村的焦虑是:赋予身体以如此重大的使命实际上是一件可疑和危险的事情,比如它经不起任何一种宗教的深度反问。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而言,正像马尔库塞在《新感性》一文中批评的:“现存社会迫使它的所有成员都使用同一种感知中介;社会不顾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未来观、出发点和背景,一味提供相同的普遍经验世界”。但马尔库塞决不赞同用身体来简单地替代或承担这种感知中介,他甚至忿忿地说:“必须彻底砸烂左右我们感官的那种恶劣的实用主义”,他把这样的生活看作是“另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制度”。北村寄希望于宗教,认为只有那种以利他和饶恕为责任的价值观才能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
道德的咎由指向身外,人身内的“动物性”也就渐渐理直气壮起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