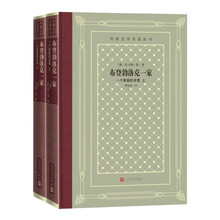爱喝糊酿酒的倔老头
小河丁丁
母亲会造两种酒,红薯烧酒和糊粮酒,半是为着供应父亲,招待客人,半是为着给我们三姐弟筹措学费,添置新衣。
造红薯烧酒,先要将红薯蒸熟,倒在大脚盆里降温,捣成烂糟,加入糊粮酒和饼药搅拌一通,搁在瓦缸里发酵个把月,这才舀到灶上的大铁锅里,用盖锅扣住;然后在灶边摆两条长凳,凳上放置冷凝缸,缸壳是双层的,内壳和外壳之间有一指宽的夹缝,外壳靠近缸底是茶壶嘴,另一头是拳头大的汽孔———盖锅上也有这样的汽孔,两个汽孔用一根胳膊长的木筒相连;接下来,缸内盛满冷水,灶下生火,大铁锅内产生的蒸汽通过木筒进入冷凝缸的夹缝,就会被那一大缸冷水凝成酒液,从茶壶嘴源源流注。那头是带馊味的红薯糟,经过一个看不见的内部世界,这头出现了香香的烧酒,小男孩拉尿一样淅淅沥沥,多么神奇呀!
在乡下,造红薯烧酒前后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动用那么多物什,算得上一项大工程,一家人都要出力。红薯储藏在镇郊茶山上的地窖里,父亲负责把红薯从地窖起出,挑回家。母亲,我们家的美酒工程师,把其余事务统统揽下,也派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任务给我们三姐弟,主要是挑水、烧火蒸酒和把红薯捣成糟。捣糟是一项快乐的工作,我们往往是一边捣,一边挑选金黄色的红薯心当点心吃。烧火蒸酒的时候,冷凝缸边上会放一只调羹,当茶壶嘴有头子酒流出,就要不停地品尝。尝酒关系到酒的品质,非同小可,必须母亲亲自把关。我太小不会喝烧酒,却喜欢尝酒,喜欢学着母亲的样子接半调羹酒,嘬入口中,咂巴咂巴,品味厚薄。头子酒薄得像白开水,等到它逐渐变厚,变成好酒,就用腹大口小的鸡公坛来接,一坛一坛接去倒进大酒缸。等到酒味明显变淡,就叫它尾子酒。头子酒和尾子酒不入大酒缸,另外盛起来给父亲喝。出了尾子酒,蒸烧酒的工程就算结束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