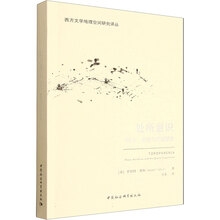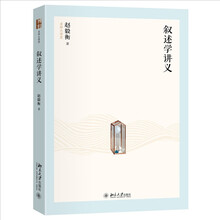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五四”之后,新文学虽然依旧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已经不能再给新文学以什么真正的威胁了。新文学的发展壮大与旧文学的日趋式微已经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就是周作人自己,在1923年1月6日所写的《读〈草堂〉》一文中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中国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在创造时代了。理论上无论说的怎样圆满,在事实上如不能证明,便没有成立的希望。四五年前新旧文学上,曾经起过一个很大的争斗,结果是旧文学的势力,渐渐衰颓下去了,但是这并非《新青年》上的嘲骂,或是五四运动的威吓,能够使他站不住的,其实只因新文学不但有理论,还拿得出事实来,即使还是幼稚浅薄,却有古文所决做不到的长处,所以占了优势。”他接着谈到在成都出版的新文学杂志《草堂》:“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虽然各地方都有,但是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种文艺的定期刊也在两处发行。”而《草堂》的出版说明新文学的影响已经从中心城市到达了相对比较偏僻的内地城市。
在周作人之前,1922年3月,胡适于《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谈及当时刚刚出现的《学衡》杂志(也就是“学衡派”)时就曾经说过:“《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