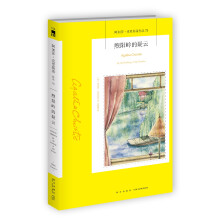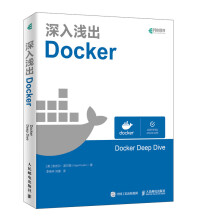历史地看,当《诗》脱离它的乐文化母体之后,其文字辞章便凸显出来成为一种思想观念的载体。诗教与乐教的区别不在这种观念本身,而在于它的存在方式和作用于人的途径。一般说来,乐教之诗并不独自表达一种精神内涵,它只有借助于仪式的操练才能释放它的意义,接受者在一种生活化的情景、氛围之中获得某种领悟。但是,《诗》的教化则是以经典释义为中介实现的,其基本方式是“礼”笺《诗》,通过“兴喻”、“正变”机制注入礼义内涵,通过“文字教”外烁于人。在汉代,今文“三家诗”很少提及乐教的理论,毛诗学的深义求解掩盖了《诗》的乐歌风貌,它的《诗大序》借用了乐论的表述来为诗的运用张目,但并不从音乐的角度解说“六义”,结果就出现了“汉儒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的情况,乐教失去了它的基础。
在诗经学史上,诗教话语和乐教话语相交织是决定古代诗学之基本结构的最重要原因。除了汉儒(特别是郑玄)与宋儒郑樵各自从“主义”说与“主声”说的立场出发,分别建立起一种彻底的诗学理论之外,古代《诗经》学者大抵便要徘徊在两种立场之间。他们在审视《诗》三百的时候,多能持一种“声歌”的视角,而骨子依然保留着有诗无乐的“义理”观念,这样他们在“主声”与“主义”的二维向度中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多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存在,表现为虽然“尊序”又要顾及《诗》的乐歌性质,虽然“反序”而又不能脱尽序说窠臼。
第二,经学话语与诗性话语。诗经汉学是一种意向性的阐释活动,它试图在《诗》文本与经学观念之间取得有效的关联,从而为经学的教化旨趣提供一个坚实的诗性认知的基础。《诗大序》就是这样一种经学话语与诗性话语相交织的文本。它的“情志合一”之论、“咨嗟叹咏”之说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与创作动因,它对诗歌体裁与表现手法的理解充满了诗意的体验,而“正变”论以及“美刺谲谏”诸说也较为准确地阐释了诗歌的时代属性与社会功能。要之,《诗大序》的确回应了《诗经》的自身阐释诉求,表面上看似一幅无关政教善恶的客观面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