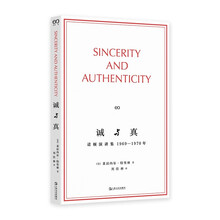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七期)》:
研究“人类共相”,远远不只是人类学的领域,实际上是现代哲学进步的重要途径。洪堡试图分析原始语言以找到前主客体关系的状态;布留尔则以原始思维作为研究对象;胡塞尔的现象学实际上追溯到人类意识的最基本功能;弗洛伊德的整个体系立足于“俄狄浦斯情结”这个人类共相的探讨;荣格等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用人类的原始共相解释复杂的社会人心理;卡西尔从原始思维中寻找人的符号起源;列维一斯特劳斯几乎完全从人类基本的族群与族群间关系讨论结构主义;皮亚杰通过对儿童早期心理发生的观察研究,试图理解人类思维的历史展开。这个单子还可以无穷尽地开下去。
研究“人类共相”,横向上,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个民族、每个社群,甚至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个个体的人;在纵向的时问轴上,研究“人类共相”,能使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甚至预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进化。尤其紧迫的,是目前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最后没有能取得某些“人类共相”(例如骄傲、嫉妒),那样的人工智能似乎更完美,实际上却暴露出重大的人性缺陷,这些过于“完美”的机器人,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甚至“人类共相”的研究使我们开始警惕与宇宙生物的接触,不少科学家警告:地外生物,甚至智能生物,很可能与我们人类非常不同,与其接触,人类就可能遇到大灾难。①除了生理的巨大差异之外,如果他们与地球人不共享一些重要的价值共相,那就不仅无法交流,甚至难以共处,没有最基本的共同善恶价值,就无法共处,还能如人与野兽那样,依靠一方“驯服”另一方才能生存。
因此,这张人类共相清单,几乎给符号学,尤其是文化符号学、符号人类学、认知符号学等,及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学等一大批学科,开出了一张课题清单。应当说,对照这张单子,我们的理论留意过的课题,以及取得的成绩,简直无地自容,研究的范围还局限于这个单子的一小部分。
中国学界往往认为普遍性太容易与“西方性”相混淆,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工作在整理中国的特殊性,以便把普遍性的“理”从西方传统剥离开来,而让中国人能够通过中国的特殊性,接受哲理所必须具有的普遍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