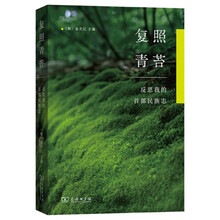垃圾生活
关于焦煤镇这一经济体,还有一个现象需要予以说明:一个意义深远的工具,离了它,焦煤镇的车轮将停止运转,焦煤镇的呼吸也将停滞。
我指的是垃圾堆。
毫无疑问,焦煤镇的生产目标就是增加产量,而且只有通过粗制滥造使产品极易破损,或者是通过极度频繁地更新时尚等方式,才能保证焦煤镇的大部分机器正常运转。只有通过疯狂的消费,才能平衡焦煤镇疯狂的生产热潮——克制消费对焦煤镇来说则是致命的。因此,在焦煤镇,没有什么是已经完成的、永久的或彻底得到解决的:这些特征都是死亡的别称。焦煤镇烧制的瓷器容易破损,制作的衣物容易磨破,建造的房子就是用来拆除的;若是之前某个能够制造经久耐用物品时代的东西存留至今,一准儿会被锁进博物馆供人们作为不思进取的遗物去嘲笑,要么就是被当成废物给扔掉。(焦煤镇偶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现实世界中的建筑,一栋接一栋,都不可挽回地毁在来自焦煤镇的野蛮人之手:我甚至见过15世纪那些无辜的半砖木结构屋舍,其前檐竟以进步为名被19 世纪的泥瓦匠抹上了灰泥。)
焦煤镇每个家庭的地位,可以从这户人家产生的垃圾堆的大小来判断。事实上,在焦煤镇的市场上每“赚一大笔钱”(make a pile),城市边缘最终就会堆起一堆垃圾,而城市的工业区也逐渐延伸到开阔的乡村地区。因此,在焦煤镇,消费不仅仅是一种必需行为,它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保持“文明的车轮不停转动”的一种手段。有时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商品生产速度过快,垃圾的产生速度完全赶不上商品的生产速度,这一乌托邦可能就会挫败它想要达到的目的;虽然这种情况破坏了焦煤镇社会组织在理论上的完善,但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却会被下面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给抵消:市场几乎无穷无尽,焦煤镇极度繁荣,最后连劳动阶级都变成有闲阶级,尽管这些劳动阶级没有受过足够训练,无法在垃圾制造方面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由此造成的混乱过程中,焦煤镇的劳动阶级开始减少工作时间,享受休闲时光,但在消费方面却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
这就是焦煤镇偶像。焦煤镇的某些特征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即使焦煤镇的一切虚伪和愚蠢都烧光燃尽,某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也依然存在:一种只专注于生产物质产品的社会环境,显然不会是美好社会应有的环境,因为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思考吃什么、穿什么:生活应该是自然、生灵和思想这三者之间的交融;与此相比,焦煤镇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一粒尘埃罢了。尽管如此,在钢铁熔炼、道路建设和行使某些工业职能方面,焦煤镇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中有了初步了解。我们没有必要忽视工业主义所具有的优点,因为它也不会包含它不具备的优点。
在一定程度上,用机械力量替代人力还是有必要的;大规模生产需要机器,劳动分工和行业分工同样需要机器;快速运输、工程师的精确计算和现代工业世界的各种其他需求皆是如此。人们甚至可能会为效率说好话,反对“多多少少做点事”(doing things rather more or less)这种想法。焦煤镇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就是认为所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好的。例如,新工厂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但是,焦煤镇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意识到,城市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一旦超出一定限度,就将不复存在。焦煤镇的座右铭是“更大更好”(bigger and better),虽然这两个形容词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它却固执地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对焦煤镇的是非评判,是基于我们使用了“在一定限度上”这个短语。在一定限度上,工业主义是好的,尤其是在新技术和电力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不过,焦煤镇则认为,工业主义的效用不可限量。
那么,“在一定限度上”究竟指的是何种限度呢?答案便是:在由人性化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中,当培养人性化的生活变得困难乃至不可能时,这个限度就达到了。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走到一起是为了生活;人们聚在一起则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这种向往美好生活的决心,是我们对焦煤镇唯一的制衡;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对此太不关心,才使得焦煤镇偶像产生的实际效果具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指出:“新发明和行业组织本该以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以此增加人们的闲暇时光,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人口剧增,劳动降级,奢侈盛行。”威廉・莫里斯认为,未来人类可能会丢弃许多复杂的机器,因为人们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生活会更幸福,工作也会更快乐。尽管大量现代组织和机器是否会被抛弃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一旦与在纸张上堆积起来并最终以不断增加的垃圾堆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利润相比,工业主义对身为组织一部分的人们的生活和幸福产生的实际影响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消除现代组织和机器还是有可能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