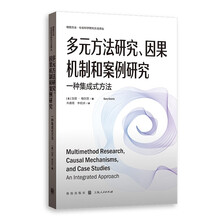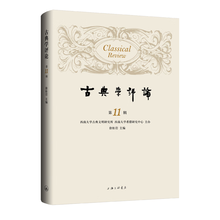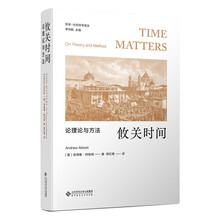在研究“文革”时期中国恐惧的基本特点时,徐贲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恐惧是人在生存完整性受到伤害和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在政治权力得到理性的控制,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毕竟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文革’期间的中国并不是这样一种社会,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成为当时极具特征的公众生活状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这种政治压迫关系来得到解释的社会心理。”诚如徐贲所说的,“文革”时期的中国恐惧形成于“文革”这种“特定社会环境”及其以“革命专政”所建立的“政治压迫关系”,它不仅是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时代性的“公众生活状态”,而且确实还“长久维持”,延续至今,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极为可怕的人性暗陬与精神遗存。比如在《随想录·我的噩梦》中,巴金就曾记述自己经常会梦回“文革”,重新经历被红卫兵殴打的“悲惨遭遇”。这样的恐惧,在见证文学的很多作者那里都有表现。比如朱正琳在《里面的故事·醒不过来的梦》中,就说自己出狱三十年来“有一个梦一直在追逐着我——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了新问题……总而言之,我又进去了”。据朱正琳说,在他平生所有的梦中,这样的噩梦具有最高的“清晰度”与“现实感”,最为真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