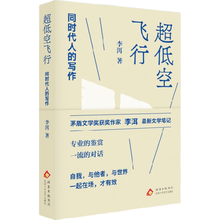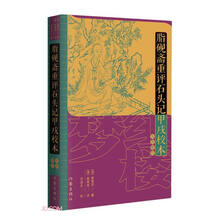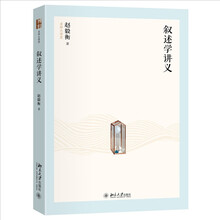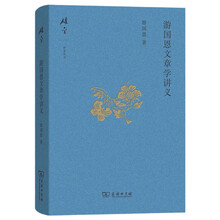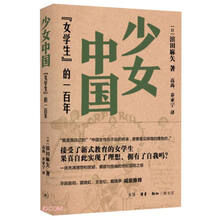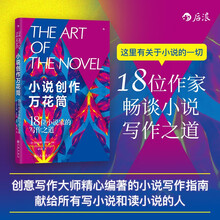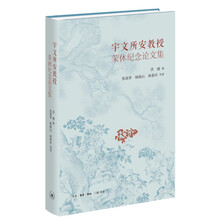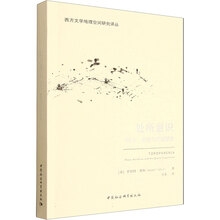《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士族审美趣味和中古文坛风尚》:
我以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经”字的理解。“经”自然是经过的意思。所谓“经过”云云,总是相对于甲地到乙地中间的某一点而言的。在“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两句中,一般读者很容易理解为是从怀县始到洛阳终的一段路程,这就会把“旧庐”当成是在怀县和洛阳之间的某个地点。这在文句的理解上是可以成立的,但与实际的地理方位则是完全不合的。这就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在写这两句话时,他心目中旅程的起点和终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既然以洛阳为终点的说法说不通,那么我们何妨改换一下终点,看看能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以为,作者在描述他的行程路线时,是把整个旅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是把怀县作为旅行的起点,同时又作为终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只要在这趟旅行中,他还没有最后返回原地,那么他途中所历,不管是顺路也好,还是枉道也好,都可以说是经过了。序文中所谓的“经其旧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事实上,这一层意思,在正文中也有照应。正文不是在清晰地交代了之前的行程之后说,“经山阳之旧居”吗?获得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对比序文与正文的表述,就会发现,二者间其实根本没有矛盾。序文只是正文的简略说法,而正文则是序文的详细描述。只是因为序文过于简略,省略了某些环节的交代,以至使人误以为“西迈”和“返经”是发生在同一时段中的两个行为。其实对序文表述的确切含义,李善早就作过解释:“言昔逝将西迈,今返经其旧庐。”将“西迈”和“返经”作为旅程中两个阶段来看,“西迈”是昔,“返经”是今;赴洛阳在前,吊山阳在后。“经其旧庐”是相对于整个旅程而言,而不是发生在“西迈”途中。这样的理解才是深得作者用心的,也是完全准确的。
解决了行程路线的问题之后,我们对向秀此时心态的理解可以更具体、真切。景元四年(263)十月以后,嵇康因为坚持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氏集团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名义杀害。这无异向当时所有的士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要么与政府合作,要么就是遭受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作为嵇康的朋友,在此之前向秀对于司马氏政权的态度,即使没有直接地表示反对,至少也是持着消极的不合作态度。我们从他赴洛后,司马昭的问话中即可看出端倪。“文帝问日:‘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说明此前的向秀一直是用避世的方式消极抵抗当局的。即使此后被迫入仕,他也并无热情,“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然而嵇康事件的发生已经不允许向秀有丝毫的迟疑徘徊了,当局就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迫使所有士人(尤其是名士)明确地表明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作为有影响力的名士,尤其是作为嵇康的朋友,向秀的出处举动受到了最高当局的密切注视。我们从上引司马昭“闻君有‘箕山之志”’的问话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管向秀的真实动机如何,从司马氏的眼光看出来,“箕山之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包含着疏离,甚至是对抗现政权的意味。对于司马氏的这种解读,向秀自然是清楚的。何况其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中,向秀的处境是极不自由,甚至是极危险的。面对着强权的高压,如果向秀不想重蹈嵇康覆辙,想要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话,除了向当局表示臣服之外,还能有什么路可走呢?应郡计赴洛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作出的,从向秀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在险恶环境中保全自己的明智的决定。我们看他在嵇康事件之前从未有过出仕的经历,嵇康一死就迅即作出应郡计赴洛的决定,可想而知,嵇康之死对他心灵震恐的程度,也可说明决定赴洛的动因了。《向秀别传》说“(嵇)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把二者的关系揭示得很清楚,这是很有道理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