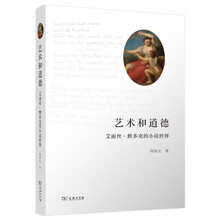《沉潜与喧嚣:当代诗歌论》:
反讽和叙事性是缪克构运用得比较娴熟的技巧。甚至早在校园时期的作品里,这两种技巧就已经初露锋芒:“大雨打湿了青年诗人的头发/他湿漉漉的脸庞灰蒙蒙的双眼/突然出现在大学集体宿舍的门口/流浪这个词逼近了我的胸口∥他的到来给我带来更为滞.重的雨意/我光着脚丫子从上铺滑下/在我落地的时候/已从他飞快的自我介绍中了解了他的一生∥这里已没有小木屋常青藤和忧郁的笛子/但我必须淋着雨带他到后街/解决他持久的肚子问题/他的深沉令另一个干瘪的诗人仓猝∥我们隔得不远/但交谈一句话往往像跑了五公里/就这样我们还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着/上帝我和他素不相识/他的到来恰让我觉得自己与整个世界相距甚远∥然后我带他回寝室/有两对恋人得了恋床癖/他定然不陌生因为他的诗句里有:/‘你的呻吟把我化为细碎’/他告诉我他痛恨——/那个一头钻进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友∥有一群人冲进我们寝室/在一副四国大战棋上纸上谈兵/他们激烈地厮杀然后喊:‘守营’‘裸奔’/他说:原来你们已经把诗歌的后现代/带入日常生活之中/这话让大家深感陌生/好在此时已经熄灯/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脸。”这里所引的是《大雨打湿了……》一诗。之所以不惜篇幅地整首加以引用,是因为经由冷冷的叙述语调和戏剧性的情节片段,该诗初步显露出一种迥异于同一时期其他诗作的风格。或者说,它是连接作者前后两个时期作品的一道重要桥梁。在这首略嫌冗长的诗作里,我们读到的与其说是对具体的某个诗人的讽刺,不如说是关于当下诗歌、艺术乃至整个文化境遇的一种讽喻。其实,时代的大雨何止打湿了那个诗人,也给诗歌乃至文学本身带来了阴霾和泥泞。
这种反讽性的主题也延伸到了后来的诗作。《醒来》一诗完全可以看作是《大雨打湿了……》的姊妹篇:“静止的一杯水让我想起什么/对一个诗人/众目睽睽之下朗诵诗作/一个诗人在电话中/将批评之作读给批评者听/对方将话筒朝向厕所”。与《大雨打湿了……》以叙事性造就一种迂回曲折的效果不同,该诗在语言上短兵相接,显得十分锋利,并且流露出深深的质疑。而《诗歌女神》则鲜明地染上了一层自嘲色彩:“一个内向的孩子失去最宠/他怎样去结识新欢/看着别人得意或拙劣的表演/他悄悄地躲向门后∥他小声的哭泣却显得那么辽远/有那么一刻/他几乎想跳出来大喊一声/可是顾虑和疑惑将他的热情化为乌有∥唯有在梦里/他才看得见她的背影/他伸手去抓/抓住了自己的一把白发”。在众声喧哗的当下语境里,那些善于表演者伪造或骗取了缪斯的眷顾,占据着歌唱的舞台。而真正虔敬的人却陷入了言说的困境。在这里,诗人以个人的写作困境折射时代的文化疾病。
缪克构诗歌的叙事性策略,也在《此夜漫长》、《判决》、《年华》等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前者写在光怪陆离的都市夜晚,一个年轻男子的“香艳”遭遇:“她们正看中了我形影孤单/或许还因为看到了我上车时手中的皮包/我的年轻正可以一点火苗即刻点燃/此夜漫长正可以一晌贪欢∥她们阻截了我三次/有一次她们飞出的吻落在了司机的脸上/有两次她们伸出的大腿照亮了路面/三次她们都口口声声说与我相识已久”。在妙笔连连的精彩叙写中,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年轻男子混合着惊慌、刺激和某种欲望的复杂心态。而诗的开放式结尾更令人叫绝:“司机放弃了他的‘起步价’/将我强行喊出他的车外/天呐!她们向我逼围过来/卡夫卡的老鼠说:天地越来越小。”这种结尾是耐人寻味的,天知道那句有些夸张的“天呐”是否夹杂着一丝隐晦的狂喜呢。“卡夫卡的老鼠”这一现代典故的运用也是恰如其分的,它像一个制动器,大大减低了这首诗由一系列动词造成的叙述速度,同时也提升了诗歌的情境。与《此夜漫长》的轻松题材截然不同,《判决》触及死亡那冰冷的面孔。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