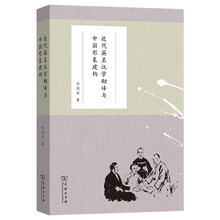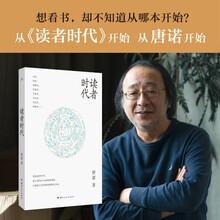格非:幻化的历史迷宫
英国小说家福特斯曾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小说完全摒除时间后,什么都不能表达”[1],正如他所言,时间不仅仅是向人们表现故事的一种标志,更是情节编排的组织者,是对现实和历史进行解构的形式化表现的重要坐标,是小说形式中的重要内核。而在格非的小说中,时间也是他的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是一项核心语码。对于格非来说,时间不仅是表现出来的形式技巧,更是主题方面的关于世界和现实的一种“时间性”母题。从1986年格非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开始,他的叙事就开始迈向一场寻找失去的时间的记忆和冥想的旅途,他不断地以“复现逝去的时光”和“还原个人经验”作为自己的写作信念。格非的小说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时间的镜像,像不断摇摆的钟摆一样,一端连接着记忆与历史的可能性,一端则不断探寻遗忘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端之间,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幻化的历史时空,不断充斥着记忆与梦幻,探索着生存与死亡,观望着欲望与绝望。而这一切的导引索就是时间这个轴心,因此有论者曾敏锐地指出格非的创作可以看作是“一场时间与遗忘进行搏斗的幻想式斗争”[2]。
一、幻象重叠的历史时空
时间以及时间性的主体经验,是格非创作早期的先锋文学方式中的核心主题。从《追忆乌攸先生》中寻找那段失踪的历史时间开始,《陷阱》中“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的没有时间性质的城市,《迷舟》中个人化的心理时间与战争时间以及历史感之间的宿命传奇,《大年》中革命、欲望与时间的斩首之间相互交结的历史诡计,《褐色鸟群》中时间与幻想性竞争关系,一直到《边缘》中被穿越的时间,格非的小说空间显然已经大部分被时间经验所占领。在格非的小说中有很多对于时间的感知,无论是“时间出了毛病”的错位的认知,还是“深陷时间窠臼无法自拔”的命运的高深莫测,或者“时间轮盘赌中的历史狡计”,都不再是简单地凸显人物的生活时间,而是关注于时间作为一种存在的探测工具的作用。在其小说《追忆乌攸先生》中有这样一句话“时间叫人忘记一切”,评论家张旭东对此深度解析并指出:“格非至今的全部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同这句格言的幻想式斗争。”他认为格非小说中的时间是一种幻想的主体对自我意识的重建,与其说“自我的困扰总是暴露出虚构下面的历史,不如说历史作为一种时间性因素总是参与了当代意识的自我构造”。[3]而这种幻想的主体,正是一种虚构的叙事主体,是一种语言主体,借助这一主体,格非使时间和记忆成为一种历史的表征,在叙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幻象的重叠,使读者步入叙述的迷宫。
《迷舟》是格非早期的先锋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时间经验成为了影响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一部以北伐战争期间的一场战事为背景的小说,萧旅长在时间的交叉小径中陷入了命运的迷舟。个人化的心理时间、战争时间和父亲的时间这三条时间线路交织在萧旅长的生命时间中,小说的叙事框架只有七天的纪事时间,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是按线形的顺序排列下来的,在小说中,格非还通过对北伐战事相关背景资料的填充和作战地图的添加,搭起了一个战争时间的叙事框架。于是,小说就在这样一种交叉的叙述框架中开始展开。如果我们只从故事本身来看,看似情节塑形的主导力量是其中的战事时间,但实际上,真正的叙事进程则是以萧旅长的个人化的心理时间为主的,他重返家乡之旅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忆的诱惑之路,就像生活在一场时间交错的幻觉里:“他踏上薄雾中的小船,遥望对岸熟睡的村子,曾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他不知急于回家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对母亲的思念,或者是对记载在他童年的村子凭吊的渴望,他觉得像是有一种更深远而浩瀚的力量在驱使他。”[4]这一股深远而浩瀚的力量会让我们觉得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的力量,但是,格非所展示给我们的却远远不是这样,而是一种时间的诡计。文章最初展现给我们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时间,严肃的战争时间以其自身的行为逻辑向前推进着,但是在萧旅长身上,我们却没有看到战争的力量,展现出来的是其强烈的诗人气质,是其划入个体的心理窠臼的私人时间,对“杏”的回忆和想念使其迷失在意识的树丛中。从表面上,似乎仅仅是简单的对于旧情人的迷恋使萧旅长迷乱在时间的海洋中,但是,这是一场命运与性格、时间与记忆的决战,这里不存在什么具体化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杏,与其说她是情人的代名词,不如说她更像是一个功能性的符号,正如张旭东所言:“‘杏’在叙事里不是作为欲望的对象,而是作为欲望的‘能指’存在着,正如‘杏’与‘性’的语音学含混似乎正好暗示了女主人公并非什么具体的欲望的所指;相反,它作为一种表征指示出欲望的存在方式。”[5]如果说对于“杏”的回忆只是一种欲望的表征,那么在他后面的追忆中,父亲的阴影则代表着更深更宏大的战争历史。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将一部战争史前史安置在主人公身边:“他的父亲是小刀会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是绝无仅有的会摆弄洋枪的头领之一,他的战争经历和收藏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军事典籍使萧从小便感受到了战火的气氛。萧常常在梦中出现马的嘶鸣和隆隆的炮声。终于有一天,他走到了父亲身边询问为什么投身于一支失败的队伍,父亲像是被碰到了痛处,回答却是漫不经心的:‘从来就没有失败或胜利的队伍,只有狼和猎人。’”[6]父亲的时间不仅包含了家族宿命的象征,更隐喻出战争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军人的胜利与否对其本人而言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仅仅是时间与历史轮盘中的一种象征筹码,“只有狼和猎人”则深层地体现出了战争的真实逻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