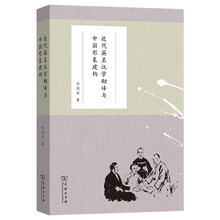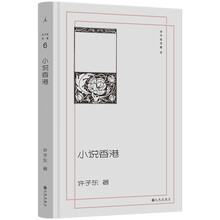《“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途中之镜》:
若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相对全面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确实具有这样一种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即便是意在颠覆、解构以往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著作,也往往无法实现思维方式的决然断裂。相反,过分强调知识范式或经验的断裂、更新,很可能只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一种偏执走向另一种偏执。①历史地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也正是处于一种不断积累经验的状态。前人的思辨,既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参照,也往往以其失败提醒我们有所防范,切勿掉进同一个陷阱,另寻苍茫大道或林间小路。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而大凡有意义的“重写”,常常是建基于经验的积累;“重写”本身也是积累经验的方式。
当然,对经验积累的强调,对思维连贯性的强调,并非意在贬低学者们的个人创造。这种强调,恰恰是为了重申个人创造的来之不易,也是为了说明个人的创造何以可能。虽然文学史写作的知识增长或再生产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但是如果没有对已有的、特别是那些颇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深入的辨析、参照、反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仅仅是原地踏步,而非另起炉灶或推陈出新。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的:“文学史写作,背后总有一些他要超越、批评或纠正的文学史的影子存在。”②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所创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几乎没有哪一本是没有经历过辩难、参照、反思这些环节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不例外。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具有明显的“重写”意图的,可看作是对“重写文学史”的重写。而这一次重写,同样建基于文学史写作经验的累积,同样具有思维上的连贯性。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始于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栏目。而“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中就已经有了极为鲜明的体现,甚至在夏志清先生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已初见端倪。①除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使得“重写文学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陈晓明语)。就陈晓明看来,上述学者的思考实践,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各自的思考也仍旧有待深入。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指出:“陈思和以‘共名’‘无名’‘民间’‘潜在写作'等几个概念为基础,来展开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叙述。这一‘重写'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突破,它非常有效地发掘了被掩盖的那部分文学事实,对当代文学史做出了新颖而深刻的阐释。但是,政治话语依然是当代文学变革的主导因素之一,如何在彰显被掩盖的文学史实的同时又不回避主流话语的影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难题。在这方面,作者使用的新概念、新术语虽然揭示出‘潜在写作’和主流文学史的紧张关系,但似乎并没有表达出更深层次的理解。”②针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晓明则指出,它“无疑是迄今为止的同类著作中最为出色的。洪先生十年磨一剑,功力深厚,其谨严与精当、准确与细致,比其他文学史著作高出一筹。只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学史图谱,揭示当代文学转折变异的深刻内涵,这是洪子诚先生给当代文学史写作提出的难题,也需要更多的书写者去面对更高的挑战”。
陈晓明的上述话语,既含有对以往学术思路的肯定与尊重,也相对隐晦地提示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到底是从哪些角度、在哪些层面上来对“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进行回顾、辩难、反思,从而形成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对话”。在另一个场合,他也提道:“如何阐释‘新中国’含义之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一个文学史叙事的难题,中外双方都深陷于尴尬之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