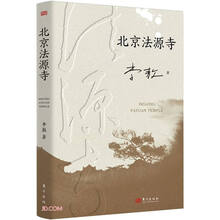(一)世俗性“日常写作”对超越性审美原则的“改造”
日常写作的早期文本实践——以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其叙事策略强调对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零度情感”的“客观化叙述”。作家对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状态下人们的生存艰辛与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进行了津津乐道的叙述与描绘,使日常生活的皱褶和沟回纤毫毕现。日常写作的低调叙事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文化失望心理,以文学的审美方式释放了社会的现代性焦虑情绪,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文学与社会、作品与读者之间日渐疏离的紧张关系。在向所谓“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过程中,文学重新获得了“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赞誉之辞。
“新写实”的文本实践作为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超越性审美原则的“改造”,不仅为已经冷清的文学重新找回了一些读者,聚拢了一些热闹的人气,而且“新写实”世俗化的审美原则开始变成一种强势的“改造”美学,其影响力量逐渐跨越“新写实”文学的边界,成为20世纪90年代小说美学的普遍性原则。诸如在“新市民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生代小说”“女性主义文学”“70后小说”乃至“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都可以看到日常写作貌合神离的“同构美学”。
如果说“新写实”作为早期的日常写作,其对经典现实主义超越性美学原则的“改造”还“心有戚戚焉”的话,那么“新生代”作为日常写作的继往开来者,则以决绝的“改造”姿态彻底与超越性美学原则实施“断裂”。朱文、韩东、何顿、张曼、述评、刁斗、邱华栋、鲁羊、陈染、林白、海南等新生代作家承续了“新写实”小说关照和描述城市日常琐事的叙事原则,一如既往地拒绝宏大叙事,而且更加彻底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性,表现出一种热爱日常事物和厌恶精神生活的世俗化美学理想。不过两类作家在叙事风貌上依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新写实”小说的写作主体与角色呈现分离状态,文本描写的是“别人”的日常生活境况,写作立场和叙述视角植根于“群体本位”;而“新生代”小说的写作主体与角色具有“互文性”,叙事策略更多选择个体本位。“新写实”作家在描写平民生态与凡庸场景时,以无法自弃的平民主义立场寄托稀薄的生存忧患与人文关怀;而“新生代”作家对都市平民的价值形态认同却产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精神位移,他们的视线偏离了平民的人道主义立场,执著于物的迷恋和欲的沉溺,“人”的退隐和“物”的凸现成为“新生代”日常叙事的变貌。①不过,“新生代”以个人化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日常写作的“改造”,拓展了日常写作的叙事领域,使日常写作的世俗化美学原则不再只是某个文学流派的叙事专利,而是“改造”成相当流行的叙事范式和写作倾向。
日常叙事就如一道流淌越来越壮阔最后四处泛溢的洪水,横贯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整体写作,逐渐生成为作家的审美无意识,支配着作家习焉不察的美学趣味。经由“新写实”“新生代”最后到了“70后”作家那里,心血来潮和不着边际的日常叙事则成为他们的文学常态。如果说世俗化审美的日常叙事,是对曾经一统天下的宏伟叙事的反叛和“改造”,使审美脱下了神秘贵族的面纱,一脸素面朝向人声喧嚣的世俗生活,那么“70后”作家文本叙事中所呈现的文本世界与日常世界的“互文性”和“零距离”,最终将日常写作的世俗化“改造”推向矫枉过正的精神迷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