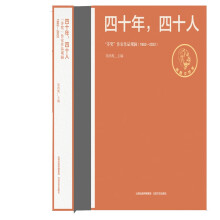吴宓对新文学浪漫主义的批判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吴宓的浪漫主义概念是笼统的。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仅停留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层面,认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就是浪漫主义。吴宓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独创,不过是照搬了白璧德的概念。吴宓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介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文章里。他的批判矛头似是而非,从未批判过国内诸如创造社这样的浪漫主义流派。与其说吴宓的批判过于笼统,不如说他缺乏新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阅读体验。与白璧德对西方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典的熟稔和18世纪以来文学思潮的深入了解相比,吴宓的知识体系要显得薄弱得多。“治西学而不读希腊三哲之书,犹之宗儒学而不读四书五经,崇佛学而不阅内典;直是迷离彷徨,未入门径,乌妄登峰造极哉?宓虽略习三哲之学说,而未尝读其著述之原本,愧惭何极!”不单是吴宓,包括其他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在宣扬他们所服膺的西方学说时,只是通过“阐释的阐释”,来代替他们对于经典的直接阅读。这个时期吴宓的日记和论文里已经出现许多西方思想者和经典著作的名字,并不表明他已经对此熟读和精通。这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学术史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
其次,吴宓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对思潮的判断与作家作品是脱节的。可以说,接触新人文主义伊始,吴宓对浪漫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作品的态度就是互相矛盾的。进入哈佛后,吴宓选修了白璧德的《卢梭及其影响》、《近世文学批评》,接受批判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思潮,他后来又选修了另外老师的《英国浪漫诗人研究》。有意思的是,吴宓一边学着批判浪漫主义的课程,一边写着浪漫主义诗歌的赏析。吴宓交给白璧德的作业是“Shelley as a Disciple of Rousseau”,交给后者的论文是“A Report on Shelleys Views of Poetic Art”和“A Report on the Sources of Shelleys Poetic Inspiration”。与其说吴宓在用审视的眼光批判浪漫主义,不如说吴宓在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欣赏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他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介绍拜伦、雪莱,并明确表示他所追慕的西方三位诗人是拜伦、安诺德和罗塞蒂,说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西洋文明之真精神”,是“积极之理想主义”,拜伦就具有“雄奇俊伟之浪漫情感”。而在新文学家阵营里,吴宓最心心相通的朋友当属徐志摩,除了在浪漫的诗情领域彼此心有灵犀,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了。对吴宓比较了解的沈从文就曾说:“您欢喜浪漫文学,浪漫文学解放人的全部心灵,却不曾将您解放。”此话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有学者认为:“在阅读吴宓那些献给女人的诗时,人们会觉得有‘两个吴宓’: 在思想文化观念上非常‘守旧’与‘古板’的吴宓和在情感生活中非常‘浪漫’的吴宓。这似乎是一种性格上的不和谐。”还有学者指出:“当他是如此详实如此坦白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动都载入《日记》并试图传诸后人的时候,这不就是再写了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至于他一边坚守儒家的传统道德,一边不顾众人反对毅然与陈心一女士离婚,然后开始对诸多女性的追求之旅,就更显得富有戏剧性了。在某种程度上,吴宓和徐志摩婚姻有着同样的悲剧性,造成这种悲剧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太“理性”,而是太“浪漫”。
今天被定义为“以浪漫主义为宗旨”的创造社,其实是一个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流派,而且吴宓批判浪漫主义的文章大多发表于创造社主要活动时期之前。1959年12月27日,吴宓回顾往事,这样谈论郁达夫:“并世而未识者,则有郁达夫与瞿秋白。斯皆宓所敬佩与笃爱……如郁达夫,其诗与小说中,具见真情性,是一浪漫文人。”吴宓从学理上讨伐浪漫主义思潮,又发自内心地欣赏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人生观之间隐藏着复杂的矛盾。
再次,吴宓对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进行批判仅停留在感性层面,是机械的理论移植。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层面,没有任何独创,不过是照搬了白璧德的概念。单就新人文主义本身而言,白璧德走进了古典主义,回归了清教徒传统,守旧的道德观念与当时西方活跃的诸多新思潮发生抵牾,是一种反潮流。白璧德对18世纪以降的文学思潮的批判显得不合时宜,也遭致许多批评。雷纳?韦勒克(Ren Wellek)就认为新人文主义就是古典主义的变种: 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稳定的人性心理,他要力图发现创作、作品与读者反响这几方面固定规则,它认为人的感受力与智力有着统一的活动,可以得出适用于一切艺术与文学的标准与模式。吴宓与后来的梁实秋一样,对五四以来倒孔反儒的反传统趋向是反感的。五四新文学所致力和倡导的主要是思想启蒙,倒孔反儒是一种必然的反封建趋势,吴宓看来太浪漫、太过分,会使世道人心因为丧失必要的道德约束而最终走向混乱:“今日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机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今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余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吴宓以儒家人文传统来理解与引进新人文主义,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解释与发扬儒家传统,这其实是一种保守的立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提倡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反封建主流思想相对立的。
同时,吴宓批判新文学,也采取了同他老师一样“不识时务”的固执立场,把激进的时代潮流视为浪漫的混乱而加以抵制。他所否定的并不是新文学的浪漫思潮,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除了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文章,他很少提及浪漫主义,更从未对国内诸如创造社这样的浪漫主义流派及其文本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论。这是一种批评的隔膜,造成这种隔膜的重要原因来自先入为主的偏见,国内梅光迪等人的通信更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这种偏见。
白璧德对18世纪以降的文学思潮进行批判,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而吴宓对国内浪漫主义的批判则更多停留在自己的感性层面,这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新人文主义批评精神的背离。白璧德在“一战”之后反思“浪漫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虽“不识时务”但不失为“一家之言”,而吴宓在国内文化和思想革新刚刚发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初露端倪之时,就挥舞大棒大加斥责,就显得机械而僵硬了。他坚信物质可以进化,但精神永恒不变,反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认定“人性二元”、“以理制欲”、“克己复礼”,这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在当代语境看来似乎是一种“超前眼光”,其实是对新人文主义机械和错位的移植。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吴宓与新文学文本明显存在着隔膜。他在美国发表批判新文学的论文,其了解国内新文学状况的信息渠道十分狭窄,主要是张幼涵、梅光迪等人的通信。“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梅君亦有书来,述国内教育近况及新潮情形,不尽感愤之意”。一个批评者,在新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远离国土,仅从朋友鼓动性的信件中了解批评对象,很少阅读具体文本,其批评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必将与批评对象形成“隔膜”。遗憾的是,这种隔膜在吴宓回国后依然存在,我们很少在其日记中发现阅读新文学文本的记录。正如沈从文所言:“您许多地方似乎同社会隔了一间”,“您的行为,您的打算,又如何与那个真的世界离远啊!”很多时候,他的精英观念让自己显得孤傲,根本不屑阅读这些不喜欢的文本。
不过,反思吴宓更应反思我们自己。一直以来,中外学者大都认可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一种人类思想的曲线,文学思潮的外延和内涵是十分复杂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学者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学思潮给出确切的定义。因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在精神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分别开来”,也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流派、思潮运动要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区分开来。正如“创造社仅仅是采取某些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社团,而不能定性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或‘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事实上,创造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连郭沫若都不认为他们是奉行浪漫主义的团体。难怪1926年,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谨慎地写道:“不讲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因为现在还在酝酿时期,在这种运动里面的人自己还在莫名其妙。”
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宓以儒家人文传统来理解和引进新人文主义,试图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解释与发扬儒家传统时,却未曾料到传统儒家道德文化体系在现代世界语境中,早已失去支撑民族国家现代建构的力量。“人性二元”、“以理制欲”、“克己复礼”,这种返归古典的人文主义终极关怀,在当代看来的确具有“超前眼光”,在现代历史语境中,却是深深的隔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