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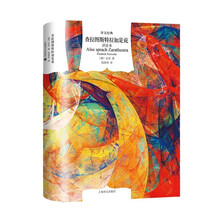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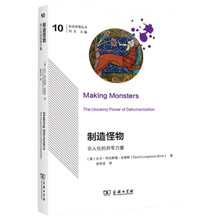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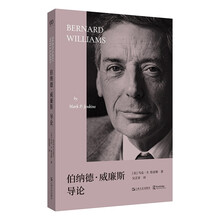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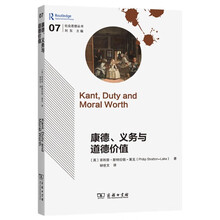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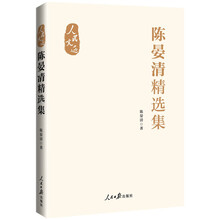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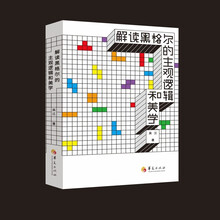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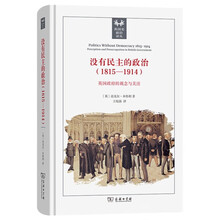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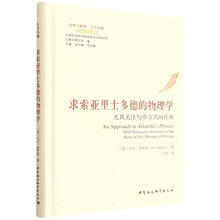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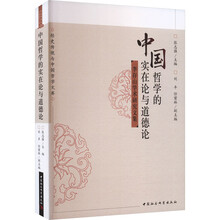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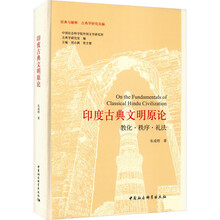
这部博士论文在卡尔·雅思贝尔斯的指导下写作并深受马丁·海德格尔的影响。当阿伦特在德国的学术生活于1933年戛然而止时,她带着这部论文流亡法国,并在几年之后带着破旧而褪色的副本来到纽约。
为什么阿伦特会选择圣奥古斯丁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生涯的起点?以爱和奥古斯丁为主题,是否也折射了阿伦特在与海德格尔复杂恋情中的体验与思索?想必这是所有熟悉阿伦特、但并未读过这部论文的读者心中的疑问。
在本书中,经过现象学训练的阿伦特,深受其师海德格尔研究方法的影响,完成的是对奥古斯丁的另类解读;她将这位圣徒转化为一位道德哲学家,在其神学思想中探寻适用于世俗世界的新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完成富有影响力和争议的政治学著作之后,阿伦特为这部早年论文添加了注释并作出修订,以她当时在政治学著作中使用的术语和概念扩大了这一探讨。
这部《爱与圣奥古斯丁》呈现了阿伦特和奥古斯丁之间的持续对话,为理解阿伦特思想提供了新视角,成为连接阿伦特海德堡与纽约生涯的桥梁。
本书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的中译本。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353-430)从未离开过阿伦特的思考范围。这部早期作品在阿伦特思想建构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她日后所达成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根源。
阿伦特从奥古斯丁所区分的圣爱(caritas)和贪爱(cupiditas)入手,避开传统的对奥古斯丁思想的神学研究,从其著作的“特殊丰富和魅力”中,“穿透奥古斯丁自己未澄清的隐微之处”,围绕生存(Existenz)概念,致力于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存在主义,从而建构属于阿伦特自己的道德哲学基础。编者J.V.斯考特和J.C.斯塔克在阿伦特本人修订版的基础上,为这本书提供了精心的导读和研究文本,构成一部非常完备的学术著作。
《爱与圣奥古斯丁》通过聚焦于阿伦特早期及后期与基督教哲学家奥勒留·奥古斯丁之间持续的思想对话,为理解阿伦特著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一版所依据的文本是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末认可的英译本,她也亲自用英语做了大量编辑,并且在准备交付克罗韦尔出版社出版时,又逐字逐句重新用打字机打出。然而,她1961年关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审判的“报告”在世界范围所引发的轩然大波,打断了这项出版计划,让她此后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同批评者的争论。德文原稿和E.B. 阿什顿(E.B.Ashton)的英译稿都藏在国会图书馆。在这两稿中,我们相信后者更有趣,因为它反映了阿伦特作为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写作者,在职业生涯的顶峰时期(1945—1975)对奥古斯丁的思考。
在阿伦特移居美国后所写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受奥古斯丁生存(Existenz)概念影响的直接证据。这些作品包括:帮助她确立作为重要公共知识分子之声望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多个版本,以及,在意识形态与恐怖的时代当中再次引起激辩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性的研究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A Study in the Banality of Evil)。2014年有一部阿伦特的传记片在影院放映并在互联网发行,此片以阿伦特亲赴耶路撒冷,决定将艾希曼定位为大屠杀中的一名“普通”作恶者,而非罕见的恶魔为题材。以这样的角度来反映一位政治理论家的生平颇为不寻常。
阿伦特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并极大地扩展了写作兴趣的范围。她不仅回归到奥古斯丁式的存在主义,而且成功说服《纽约客》杂志让她前往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现场做“记者”。虽然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确定,但阿伦特是一位尊重事实的评论者和求真的理论家。在对1982年伊丽莎白·杨布鲁歇尔所著阿伦特传记的一篇评论中,《纽约时报》称她为“世纪女性”,正如该报所称,阿伦特已成为一个“非常美国式的成功故事”。因此,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表明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如何作为桥梁,沟通了她1929年的工作和到美国后的研究计划;因为这一时期她重新发现奥古斯丁的编写工作也在酝酿或修订当中。
2014年在欧洲和美国重新掀起的这场对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持续到2015年。由于阿伦特将出现在玻璃箱内的那个男人描绘成一个循规蹈矩的职业纳粹,既不能批判思考又不能真诚言说,艾希曼这一标志性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分外耀眼。最近斯坦格尼斯和利普施塔德的两部研究艾希曼的专著便是这场争论影响下的代表作。两人都聚焦于艾希曼事件及一个密切相关的议题——阿伦特对艾希曼罪责的著名解释。斯坦格尼斯做了大量的档案研究和实地采访,并结合艾希曼的具体处境——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南美避难地——来审视他。利普施塔德则回到艾希曼审判本身,这些批判皆指向阿伦特作为作家的冷峻、嘲讽风格,又批评她未能聚焦于艾希曼信念中的反犹主义内核。
利普施塔德指责阿伦特说,她的书写主要唤起的是对她自己非凡散文风格的关注,她的笔尖充斥着几乎对所有牵涉审判的当事人(包括辩方和控方)毫不留情的攻击。阿伦特被指责为“对造一个漂亮句子的兴趣甚于了解其效果”。这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同杀人凶手艾希曼“犯了同样的罪过”,即从不考虑她的言辞会伤害全世界的犹太人。然而,利普施塔德的错误在于未能做出一个关键性区分:阿伦特只是想着把自己的书写当成一份她所谓“讲述真实”的演练,而不是像艾希曼在法庭和日记中,以夸大其词的陈词滥调作为掩盖个人罪责的烟幕弹。相反,阿伦特故意用手中的笔让读者震惊,叫他们“直视”那些她眼见的事实,颇像奥古斯丁直视罗马帝国后期的道德伪善时所用的那双清醒、真实、毫不躲闪的眼睛。阿伦特也用远处的广角去判断作恶者和旁观者,包括艾希曼的裁决者本·古里安(Ben Gurion),和那些希望通过列出犹太人名单和给出照管物资来躲避盖世太保攻击的犹太人聚居区领袖。
斯坦格尼斯的著作是对同一条种族灭绝之路(这条路的地基是艾希曼为其公共生活的不同阶段——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公仆、阿根廷的德国流亡者、因种族灭绝而受审的囚犯——竭尽全力的伪造和粉饰)的详尽的、历史学的重访,其中包括了对数篇艾希曼被捕前在阿根廷接受萨森(Sassen)访谈的精读。在这些访谈中,艾希曼对“犹太人问题”高谈阔论,十足一个情愿而得意的管理者。斯坦格尼斯认为,这种前后不一证明了他后来在耶路撒冷给人的翻转印象是在故意撒谎。在那里,艾希曼故意将自己表现为一副几乎不能自圆其说的官僚形象,而这个官僚似乎对其发动的屠杀毫不知情。斯坦格尼斯承认阿伦特的艾希曼肖像就本身来说是精确的,但她认为那是短视的,因为阿伦特未能进入对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的最近几十年研究,包括萨森的数篇访谈。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在阿根廷表现得很明显,同样的形象却没有出现在耶路撒冷。不过,斯坦格尼斯还是称赞阿伦特无畏的报道,称赞她既不在以色列法庭的政治面前,也不在艾希曼令人惊骇的“事实”面前退缩。而这些“事实”就是,艾希曼将自己表演成一个平庸官僚,用以冲洗掉那些同样有力的事实证据,即他无情地将犹太人运往死亡之路。
然而,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并不需要萨森的访谈。她在报道的同一时期致力于奥古斯丁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艾希曼现象的模式。她确实通读了全部庭审记录,但再多关于他在阿根廷的那些纳粹主义自吹自擂的一手报告,也不会改变她就“显现在面前者”得出的结论。她所看到的艾希曼,是陷入到奥古斯丁所描述的受死亡驱迫的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中的居民。他完全被自身的平庸以及这种平庸对他野心造成威胁的恐惧所消耗;他的中下阶层出身、低教育水平和早期的寂寂无名,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世俗的死亡。为了摆脱这种因害怕永远不能获得他个人渴望的一切而产生的恐惧,艾希曼在纳粹等级制里寻求不断的称赞和奖赏。因此,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至真实的死亡。在这过程中,他还为“小人物”发明了一种“康德式”的道德以迎合那些有权力支配他的人的期望,这种道德将德国中产阶级的社会价值和元首的授权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在坚称那个在耶路撒冷的胆小怯懦而又雄心勃勃的低能儿是真正的艾希曼(即使其核心空无一物)这一点上,阿伦特是对的。
中文版序言:为何是奥古斯丁?
序言:重新发现《爱与圣奥古斯丁》
致谢
爱与圣奥古斯丁
导 言
第一章 作为欲求的爱:期待之未来
一 欲求的结构
二 圣爱和贪爱
三 爱的秩序
第二章 造物主和受造物:回忆的过去
一 起源
二 圣爱和贪爱
三 邻人之爱
第三章 社会生活
重新发现阿伦特
引言:“新开端”
思想轨迹
海德格尔: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阿伦特
雅斯贝尔斯:阿伦特与生存哲学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一部让我们理解阿伦特哲学与神学思想之根基的主要著作。
——让-贝蒂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芝加哥大学)
阿伦特的作品迷人且极为重要,而斯考特和斯塔克的工作使得它易于被英语读者所理解。我将其郑重推荐给任何对知识史和阿伦特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或学者。
——杰弗瑞•C.伊萨克(Jeffrey C.Isaac,印第安纳大学)
编者极为清晰且翔实的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阿伦特的生平与思想,尤其是关于她和海德格尔及雅斯贝尔斯的关系。
——《选择》(Choice)
本书启发我们重新思索传统上对阿伦特思想的解读。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斯考特和斯塔克关于阿伦特思想之演化的结论令人信服。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我们是阿伦特、圣奥古斯丁还是现代性自身的学徒,都该感谢这两位编者。
——查尔斯•T.马修斯(Charles T. Mathews,《宗教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