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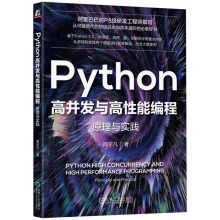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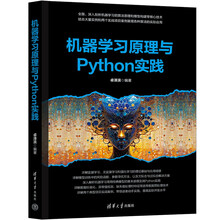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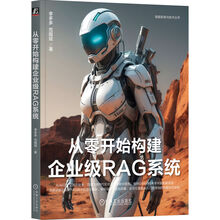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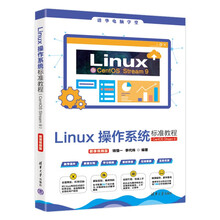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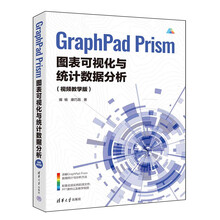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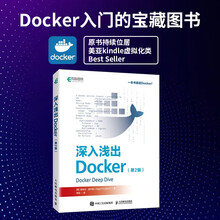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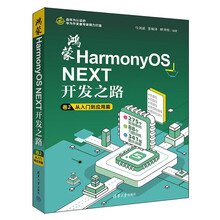
《法的中国性》是一本立宪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表达的杰出著述,探讨在近代中学与西学的激荡中,民权、民主、宪法等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制度的创新,对其中国实践作了历史和语言双重维度的解释,对当下尤具启发性。
其一,命题之大。民权、民主、宪法何也?乃中国宪政文化之核心内容,此乃中国有识有志之士述论百年有余而未解之题,亦是国体政治之实质问题。
其二,蕴含之大。民权、民主、宪法虽为政治问题,但却是历史文化的生成,所以它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特质,无论是中国式的民族诉求,还是西方式的宪政诉求,实际有极为深刻广阔的历史文化内涵,涵盖了许多社会政治、文化、道德问题。
其三,眼界之大。谈民权不能不谈民本,亦不能不谈民主。但同为近代性话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如何?是自生还是他生?是主动创造还是被动回应?上下几千年,纵横东西方,作者一一涉猎,无开阔大眼界,绝难把握。
其四,文魄之大。开篇破题、立论和批判,不数言已将述论推向颇高的境界,将古今中外的同一或非同一话语连接诠释,贤人智者招之即来,呼之听用,颇有作宇宙文章之势。
其五,功夫之大。文章读来,每件探微钩沉,旁征博引,逻辑严谨,思考缜密。细细品之,知其决非一日之功所能成就。
此商品有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法的中国性》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础性概念(比如民权、民主、宪法等)以及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劳教制度、法家思想等的一种开放式研究,从跨语际实践及词源学的角度阐释和辨析了民权、民主、宪法、水、治、法等的起源及其流变,对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
《法的中国性》旨在说明:
1、中国近代有关宪政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观看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政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主要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政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直接的意思;同时,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西方的宪政是因为西方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的“非优越性”这样一种中国式体认被中国接纳的。
2、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对西方宪政原理如何取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问题的体认以及体认的方式。而决定这种“体认方式”的,不是西方宪政原理,而是由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提供的智慧,以及对智慧的化用。当西方“宪政”剥脱了原有的语境被置于异域场景之后,其意义与价值必定会发生移转。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这种移转本身,而是移转的意义:“移转”并非是中国对西方的“误读”,而是一种主体性的主动选择。
3、晚清、民国期间西学的引进之于中国的意义不能被无限的夸大,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外部文化,但强加的不行。
1我只是要说,一个中国的民权主义者并不是一个不懂西方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意识地拒斥了西方某些东西,因而一个中国的民权言者首先是一个通晓“西方原理”的人,哪怕只是一种肤浅的方式。一个手持长矛杀死传教士的“义和团”乡民不是中国的知识者,仅仅是个勇莽的战士,而一个中国的知识者则意味着他知晓中国需要什么,如果这被看作浅薄,那也是一种必要的浅薄。
2中国过去的圣人们对百姓的读书识字不感兴趣,现在的圣人们的“开民智”则是要把人彻底变成瞎子,以便于他们永远需要引领者。当我们为儒家“民为贵,君为轻”的话语感到欣慰时,千万别忘了,那些被视为“尊贵的人”都是些没有瞳子的盲人。中国的民权意蕴由“开民智”的言路全部托出了。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权就是让这些不知不觉的人当皇帝(这叫人民掌握政权),另外再让先生那样的先知先觉者组成政府(这叫政府掌握治权):“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个很安全的接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便知道用他,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思想做成事实。”
3中国法家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坏名声,他们往往被看作当权者玩弄伎俩诈术而出谋划策的法术之人。近世以降,中国学者虽然出于国家、民族问题的功利性考虑,重新体认法家“富国强兵”思想的重要性,但对其法律思想则作了许多不恰当的解释和评价。法家的法学传统在当代中国虽已碎裂,然其余绪并未中绝,思想的碎片散落在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之中。它的“尚法”“尊法”精神暗合了当代中国推行法治的潮流,“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的官方文本和法科大学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便是一例。无论我们的学者怎样煞费苦心地去辨析“依法治国”与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有何不同,凸显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则绝对是法家的理念。如果把当代中国有关法治规范和概念认知的“知识话语”与“权力话语”这两个文本相对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法治图景”里,西方的“原教旨价值”更多的是皮相,而其底色则是传统的法家思想。法家有关法的许多见解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问题的“遗传共业”。虽然不能把“以法治国”作为现代法治概念加以使用,但它无疑是法治概念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4如果说,一个历史的文本必须表达“现在”的欲念,不管这种欲念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拟的,那么,七五宪法肯定是有“重大缺陷”的,因为它所表达的恰恰是“现在”急于要嘲讽和遗忘的东西。如果说,一个历史的文本要恰当地表述那个历史的话语和实践,而且“现在”的“我们”不仅仅把历史简单地看作过去,或者看作一个过程的完结、一段时间的末端,而把历史看作“现在”的在场,“他们”也并非“我们”异己的他者,那么,“我们”既无法也没有超越历史,而对这个“重大的缺陷”的发现也就不是不言而喻的。
“重大缺陷”的发现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基建于现实优越主义之上,依据的是今人必然优于古人,现在必然胜于过去的现代主义。这个方法由两个既相关联又有不同的方面构成:一种表现是,基于现在话语实践的优越性,映照历史的话语实践的低下性,而在这种映照的过程中,又预设了七五宪法文本是这种低下的话语实践的准确表达者这样一个逻辑。“重大缺陷”就是这个逻辑逐步展开的结果。在这种发现上,一边是现实优越的词汇,比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一边是卑下的历史词汇,比如自力更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委员会、党的一元化领导。两者价值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对任何一个“现在”的“我们”来讲都是不言自明的:“重大缺陷”就是优越的现实词汇的反面。问题是,“现在”有权利要求历史用我们喜好的现在“词”去表达相同或类似的“物”吗?如果有,那又是谁给的这种权利?
9宪法(constitution)并不起源于社会契约,它是后来被那些社会契约论的信奉者们“社会契约”化了的,或者说,“宪法是社会契约”是西方那些信奉“社会契约论”的立宪主义者对宪法的一种解释方法。只是,这种解释方法不但改变了“宪法”概念的原意,而且也重构了西方宪法的历史。这个宪法的历史可以被称为西方的“宪政历史”——因为社会契约论,宪法的历史被宪政化了。
10“时间”是需要隐喻模型的理智概念(intellectualconcept),即是说,由于时间不是具体实在,我们需要某种物象或模型以便将其概念化。所以,我们思考时间的方式,是我们把思想基于其上的隐喻的必然结果。现代的人们“倾向于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有限的资源或商品”,时间通常被现代人设想为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节省或花费;投资,预算,筹借,共享或吝啬;赢得或失掉”。比如,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甚至我们的行为也通常依照这种思路。用来将时间概念化的本喻的差异,是区分中国和西方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任何学问都需要依赖一套系统化的术语或词汇进行思考和表达,术语是用于思想理论化的抽象概念,学问和思想实际上就是这些术语和概念的组合,而借以表达某种学问和思想的语言又不可避免地以具体意象为基础。
11在有关作为“准(绳)”的“法”的早期概念中,“水”大体提供了两个面向,一是由治水的丈量工具所提供的对“水”的“规范行为”(引水入河道)经验的援用:“准绳”对治水的意义对“治人”照样有用;二是中国古人对“静止的水”的观审中,体认到水自身所具有的“准绳”意象。荀子、庄子以及孔子对静止的水的物象所建构的“法”的意义,是中国法概念不同于西方罗马—日耳曼法文明最为精彩的一笔。
14“近代”是一个困局,中国身陷其中,被囚于此。如何挣脱突围,是对这个民族智慧的考验。它关涉两个问题:如何认识自我历史的价值,并以此来重新评估祖传的智慧是否管用;如何审视造成这个困局的西方,包括它的器物和典章制度。毫无疑问,中国自遭遇西方开始,就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打量与观审。这也是祖传的智慧之一,古老兵法的运用。而如何观看西方的模样与价值,是与重新估价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在同一个空间而未必在同一个时间线轴上进行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中与西”“新与旧”交织的复杂关系。由近代建构的这种关系,用惯常的诸如“一般性与特殊性”(西方性与本土性)、“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我者与他者)等范式进行解释,在我看来都不像鞋与脚那样合适。这其中,中国宪制思想为之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15“中国宪制思想”这个用语实际上涵括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中国近代有关宪制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观看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制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主要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制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最直接的意思。“挪用”是中国在构造自己新的心像时对西方的一种免费借取,无须返还。而相反的,中国传统中并不具有这样的思想,更没有以此为轴心所形成的完整体系,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
还有另一层意思。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任何一种外来思想的移入都是以自己的“理解”为前提,构成这一理解的首先是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包括使用的语言文字、词语概念、思维方式,以及身在的语境。这个“前解”是通向“理解”的不可绕越的起点。没有祖先的遗迹——文字,外来的思想就无从书写。这样的书写与其说是对外来思想的复原和重述,毋宁说是意义在异域的移转与再生。“我者”本身构成了意义的再生之地。
16为什么“民”会成为中国宪制思想的关键词?这是一个可以反复咀嚼而未必能够咽下去的问题。拣最容易的一点说,有关“民”的思想所承载的首先是中国自己的古老智慧。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中国宪制思想的第一块踏石。只要有关政事,儒家和法家总是喋喋不休。法家被中国近代思想冷落,自有它的道理,盖因它对君主主义的热情鼓吹淹没了它自身的智慧;而儒家对百姓(民)所说的那些廉价的奉承话,更容易打动那些认为皇权该为中国衰败负责的人们的心。儒家在中国近代宪制思想中是一个双重角色:从对它进行委婉地批评到之后的猛烈攻击,一方面,儒家文化成了中国屈辱的替罪羊,而且是一个合适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思想无论对它有多少怨恨,对西方宪制原理的挪用又必须借助于它所提供的语汇、概念和资源。
17近代中国在为自己的“现代国家”构图时,存有一个既定的格子:格子的中央是强大的优胜者——西方,贫弱落败的中国则被挤在格子之外。然而,无论中国处境多糟,它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意义上的尾闾,尽管西方自己可以这样看。中国曾是另一个世界的主宰,它把这个世界称作“天下”,而自己则是这个世界的首都。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相遇”以及相遇的方式,是生成中国无尽烦恼与纠结的真正根源。对中国而言,(与西方)“相遇”这个词含有诸多复杂的意义。最主要的是,无论中国在这个世界的处境怎样,它都不可能放弃五千年积攒起来的那个“大国”的主体身份——曾居于中心位置的人不可能甘愿在人群中坐在最后一排。而复杂性还在于:想要重回自己的主体位置,似乎首先得忘记和放弃自己的主体身份。一方面,中国不得不从心理层面而不是从姿态上真正面对西方;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与自己的文化历史割断。无论传统是被看作负面的障碍物,还是一种可以援用的资源,都是如此。面对西方的同时,也得面对自己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