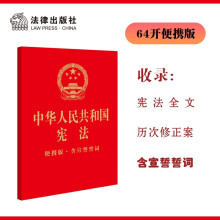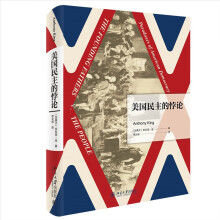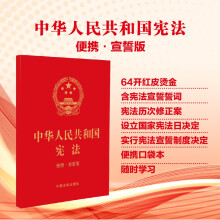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演说 * 中说:“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克林顿总统冷嘲热讽般地缓和了共和党的那些政治话题,从而保护了他的总统职位,因为在之前1994年的选举中,克林顿的政府策略明显是被公众反对的。当时,共和党人是自1954年以来第一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同时获得了多数席位。许多传统的民主党人认为,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发起的“新政改革”(New Deal agenda)以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实施的“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s)发展出来的——且为民主党所秉持的——那些原则,已经被克林顿总统背叛了。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克林顿总统的这番言论。他的表述说明了他的一种理解,那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宪法新秩序已经得到了巩固。通过宪法秩序(或政体)这个概念,我想表明的是:某个时期会存在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而国家的重大决策都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得以持续地作 出,而且经由原则来指导这些决策。 [2] 这些制度和原则会产生一种结构(structure),由此让一般的政治主张都置身其中。这也是为何我把它们称作是宪法的(constitutional),而不仅限于政治(political)。 [3]
由此,机构(institution)和原则(principle)构成了宪法秩序。在机构层面,宪法秩序并不限于最高法院这一个机构,也包括全国性政党组织、国会以及总统。实际上,就如我在第一和第二章中所主张的,如果不考虑可以主导其他联邦机构的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这个语境,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最高法院所阐释的那些宪法原则。对我而言,宪法秩序更像是小c开头的英国宪法(consti- tution),而不像我们所说的美国宪法(Constitution)这样一部文件。而且如同一些研究宪政的学者所发现的,研究英国宪法会更奏效,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宪法秩序的研究,如果我们超越司法教义(judi-cial doctrine)以及成文宪法(written Constitution)这个层面,进而放眼那些相对稳定的政治安排以及指导性原则,那么,这样会更为奏效。
在1944年的国情咨文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对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宪法秩序中的指导性原则进行了界定,而我则把它称为“新政—大社会”(New Deal-Great Society)宪法秩序。罗斯福呼吁落实“第二权利法案” (Second Bill of Rights),其中包括“有权利丰衣足食及娱乐”,“有权利有病可医、居者有其所、接受良好教育”,以及“有权利在老龄、疾病、意外事故和失业时获得充足的经济保障。 [4] ”当然,克林顿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消极怠工。应该说, 新宪法秩序中的那些改革动议都是小规模的。而罗斯福在“新政—大社会”宪法秩序中所表达的那些雄心,在新的秩序中也已被消磨了。
最常见的是,那些指导新宪法秩序的原则所达到的情形是:直接通过法律(Law)来追求正义的那种雄心,已经在根本上被消磨了。让个体责任与市场过程——而不是国家的立法——来确认并努力推进正义,这已成为实现雄心的手段。与过去新政—大社会政体的情形相 比,法律(包括宪法)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它们在新宪法秩序中所直接扮演的角色比以前要弱化许多。法律与宪法原则设立了很多条件,由此可以让个人和组织努力去追求他们的自身目标——包括一些人可以由此来追求正义。当然,法律和宪法原则也搭建了一个架构,由此 让这些努力都可以置身其中来展开。换句话说,新秩序下的正义图景 vision of justice)是:政府只为个人搭建一个架构,从而可以让他们置身其中来追求自身的正义。
当 然,宪法秩序也会逐渐被修建,乃至转型: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于其中发现一套枢纽式的制度与原则,其中有一些来自于先前的政体,也有一些可能是从那些对之后政体有激励的制度和原则中引申而来的。 [5] 如同我在第一章里所提出的,当前的宪法秩序最初成形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选举之中,接着在1994年的选举中,它在内容上更为确定,然后在克林顿任职的最后几年,又得到了加固。这种政体修建与转型的逐渐过程,很难被描述为“某一种”宪法秩序,因为总存在一些需要考虑的特征——这些特征有的是过去留下来的,有的是未来可预期出现的,因此并非只是考虑当下政体的某个核心特征(central feature)。诚然,我对这些核心特征的描述可能并没有达到其本来应有的面貌,当然,如果总认为我的观点只是一种尝试(tentative),那么可能会对内容的理解有所影响。
在本书中,我比较了新宪法秩序和“新政—大社会”宪法秩序。从我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再从美国宪法史中去挖掘其他类型的宪法秩序,但就此而言,似乎要把我所使用的方法与宪法学中其他两种紧 密相关的方法予以妥当地区别开。 [6] 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把宪法的历史描述成:长期维系的日常政治(normal politics)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 [7] 阿克曼的日常政治时期 大致可对应我所说的宪法秩序,而他所说的宪法时刻也许就是新宪法秩序出现的时刻。
根据阿克曼的观点,法学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M.Balkin)和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也对宪法秩序中的“革命性转变”有相关论述。 [8] 在强调这些转变可以——而且一般来说也是——逐渐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赞成阿克曼。他们间接地批评了阿克曼所使用的某一时刻(a moment)这个隐喻——该隐喻以此是要表明宪法秩序的形成是迅速的(quickly)。至少就新宪法秩序而言,这具有误导性。 [9] 对于巴尔金和列文森来说,宪法变革要通过他们所说的“政党巩固”(partisan entrenchment)过程来发生,其中某一政党通过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有时是迅速、但时常是逐渐地——来获得对三个政府权力部门的控制。巴尔金和列文森以布什诉戈尔案 ( Bush v.Gore)为背景来架构他们的力作。他们把该案中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就任总统看作是政党巩固过程中又一个得力的棋子。通过这个案件,最高法院那些保守派法官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 以确保下一位被任命的法官能进一步巩固共和党对法院的控制效果, 从而完成政党巩固的任务——政党巩固是宪法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 [10]
我并不同意阿克曼的说法,反而赞成巴尔金和列文森的观点,也就是宪法政体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某一些突发时刻(convulsive moments)完成的。比如,从第二章中讨论的一些最高法院判决,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政—大社会”宪法 秩序的衰亡,且可以看出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人知的原则其实是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不过,巴尔金和列文森强调政党巩固,意味着他们不可能考虑到一种情形,即宪法政体也可能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持续分治的政府(divided government)——我在书中对此进行 了探讨。而意识形态分治的政府各自用他们自身的指导原则来制定政策。对巴尔金和列文森来说,布什诉戈尔案已经把我们放到了宪法变革的边缘。不过与此相反,我倒认为我们已经向新宪法秩序转型了。
我与阿克曼在方法上的另一个区别是:阿克曼强调对宪法时刻的识别,因为他想提出一种“规范宪法理论”(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theory),由此可以来解释他所说的宪法上的时际困难(intertemporal difficulty) [11]并就“人民在多年前所做的决定为何还可以在当下约束人民在行为上的选择”这个问题作出解释。阿克曼认为,在宪法时刻期间所作出决定的规范权重(normative weight)比在日常政治状态下的要大,由此便解决了时际困难。 [12] 这是因为:与日常政治时期相比,宪法时刻期间所产生的政治结果是能够吸引公众更为关注那些“宪法要义”的(constitutional fundamentals)。日常生活状态下的那些关注让许多人远离了政治审议(political deliberation)以及允诺,当然,这也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合适的,从而也只会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关注一些利益群体,并以此来影响政策的发展。当然,这些日常状态比宪法时刻要多很多。
阿克曼的这些规范考虑使得他要去构建一些形式标准,而且在他看来,只有达到这些标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某个宪法时刻发生了:因为对宪法忠诚的那些义务产生于宪法时刻,所以人民要弄清楚究竟在哪些具体的场合下会出现这些义务。与阿克曼相比,我很少关注时 际困难方面的规范难题。 [13] 基于此,我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去满足一些 特殊的形式标准,从而来证明新宪法秩序是否已经产生了。 [14] 比如,并不存在某个特定的关键性选举。 [15] 虽然阿克曼对我们宪法秩序所进行的思考已经影响了我的方法,但我相信,阿克曼这种来源于规范性关注的形式主义,会让我们看不清当下的宪法秩序究竟是什么。
阿克曼的形式标准确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们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宪法秩序何时代替了另一个。然而,我的方法没有阿克曼那样来得爽快。我不依靠任何形式标准,当然,我也会对“哪种制度安排和指导原则可足以稳定地成为宪法秩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作出相应 的判断,不过其他人对此可能已经做好争辩的准备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尽力去为我的这些判断进行辩护。第三章则向大家展现那些挑战我的这些判断的情形,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所做判断的说服力。但是最后,我仍然认为我的判断是靠得住的,至少,我希 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我分析过程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地方。
由于阿克曼关注时际困难,这也使我与他在方法上有另一个不同之处。时际困难和那些指导宪法秩序的原则在司法适用(judicial en- forcement)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困难是我们担心自己受制于那些多年前所做的决定,并且让法院来发布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指令。与阿克曼、巴尔金或列文森相比,我在政体原则上所使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只以法院为中心。与他们不同的是,我相信宪法原则可以——并且正是——通过连贯性宪政体制中的法律(statutes)得以呈现出来。对于“新政”宪法秩序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罗斯福所提出的“第二权利法案”与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样,都具有重要性。对于“大社会”宪法秩序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没有办法与1964年的民权法案、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以及那些政体指导原则(regime's guiding principles)下的医疗保障计划相匹配。当然,宪法秩序中的那些指导原则也会影响一些司法判决,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仅仅局限在法院,那么对于“我们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这个命题,我们就会在认识上有所偏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