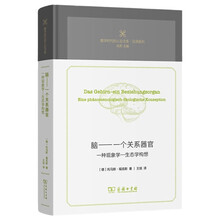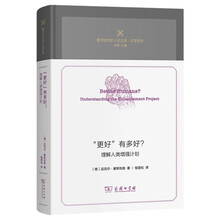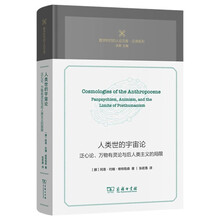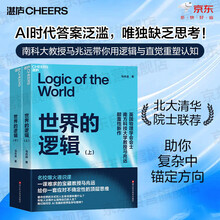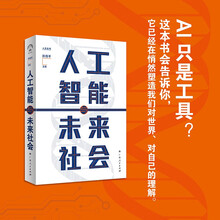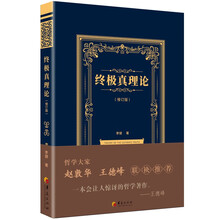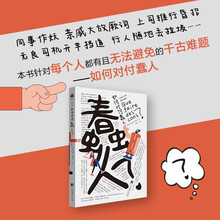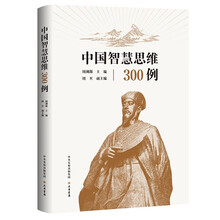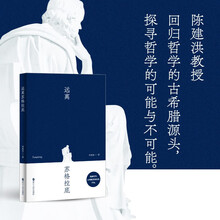知识的急剧发展及其物化应用所带来的这种双重影响体现在当代人的进步意识中,即对进步抱有幻想与失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理性意识呈现出的并存态势。而这两种理性意识体现在进步观念上就是理性乐观主义进步观与社会危机论的共存。
理性乐观主义进步观通过对理性的弘扬和知识的不断积聚而在近代逐步确立起来。早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就体现了这种理念的萌芽。弗朗西斯·培根则极力高扬知识理性,强调知识理性及其物化成的技术行为与技术手段可以“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的事业和便利”,并明确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从而开启了一个知识累积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笛卡尔的为知识理性提供理性原则及思维方式,不仅哺育了整个欧洲近代哲学,而且为理性乐观主义进步观的确立与演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一举确立了知识理性在社会发展中“君临一切”的独占性地位。而孔多塞则干脆把人类进步的历史概括为人类知识理性不断进步的历史。其后,知识理性经过康德、黑格尔、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确证与弘扬而逐步确立了其崇高的地位,人们开始坚信理性是万能的,知识及其物化的技术行为与技术手段可以战胜一切,并最终确立了理性乐观主义进步观在社会进步观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知识的快速发展和知识力量的迅速扩张,知识及其物化的技术行为与技术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日益凸显,这使得原有的理性乐观主义进步信念因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逐渐动摇,在这期间,一个与其相反的有关社会进步的悲观主义理念开始萌芽并迅速崛起。其典型代表是罗马俱乐部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所持的悲观主义论调。他们在具有全球影响的著作《增长的极限》及其系列报告中,强调知识及其物化的技术行为与技术手段不顾后果和不加限制的应用,已经使人类陷入发展与进步的困境。其显著后果就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进而造成社会的危机与人类的困境。他们认为正在变化着的令人困惑的世界形势最终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因此在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刻变化的时代,人类要不容置疑地意识到世界问题的存在,并且取得选择发展模式的优先权,做出必要的决定以求得问题的解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了困惑和危险……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各地呈现出紧张的不论好坏的戏剧性局面:一方面最神奇的繁荣背后显现出核灾难的恐惧,另一方面正当的生活希望,至少对下一代人来说是这样,淹没在无法逃避的悲惨灾难之中。”①在其他的许多相关报告中,罗马俱乐部也从不同的社会发展侧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前景做了种种预测,提醒人们在知识社会中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世界的未来是不堪设想的。罗马俱乐部的这些理论担忧无疑使立足于征服自然、发展知识理性的进步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工具理性的大力抨击而大肆颂扬批判理性的理论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以悲观为基调的社会危机理论开始在西方社会逐步确立并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进步意识并存的社会态势。
五
正当人类陶醉于对大自然的征服与统治之时,知识及其物化实践所带来的危机蜂拥而至。甚至可以说,知识及其物化的技术行为与技术手段在为人类建造天堂的同时,也为人类准备了地狱,知识一下子也由天使变成了魔鬼。面对知识及其物化的技术行为与技术手段给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造成的“窘境”,知识理论界为了找寻其解决的合理路径,纷纷举起了批判的大旗,试图厘清知识与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本质上说,批判是知识理性的天然本色和应有之义。人们在接受与应用知识理性的过程中本身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②。批判也是人类超越现成现实、追求知识、实现理想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批判的理论预设与前提就是对现存事物或现有理论的否定。因此没有批判也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与理论的发展。同样,一个缺乏适当的理论批判空间与实践批判余地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活力与缺少动力的没有发展可能性的社会。正如雷沛鸿先生所言:“人类的文明进步有赖批判精神的存在,否则社会生活将停滞不前,甚至流入僵化没落,……只有容许批判的余地,才有好的社会和好的个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