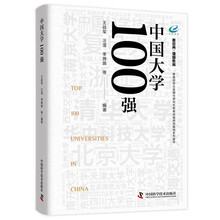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某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