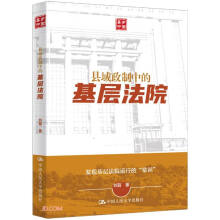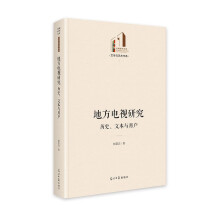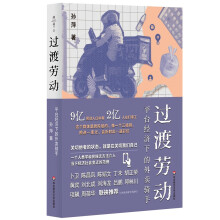《分化与整合: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
绪论:社会转型呼唤民族研究的社会学思维
一、社会转型与西北民族问题研究
研究当前的民族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因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曾用四个“深刻”来概括当前中国空前激烈的社会变迁,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相应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地处祖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同质型社会结构开始解体,逐步向异质型社会转变。具体来说,社会转型期,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无论在水平方向,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分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①阶层分化,即社会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声望资源、关系资源等)从相对均匀分布转变为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②民族分层,即社会经济资源在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的不均衡分布;③利益分化,即不同民族、阶层、群体或个体的利益诉求表现出异质性;④观念分化,即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随着社会变迁不断趋于多元化和理性化。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有机体从单一功能向多元功能的进化,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功能主义者强调,分化是经济结构增长、社会群体重组的标志,等同于现代化过程,代表社会系统一个单一的变迁方向,其社会影响力无处不在。但分化的趋势一定是新近分化的各单元、各阶层之间重新的社会整合,因为每一阶层、每一单元都具有专门的功能,只有相互依赖和交换才能满足自身和整体的发展需求。总之,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分化的看法是积极、正面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与功能主义相反,冲突主义指陈,社会结构分化使不平等因素增加,社会冲突加剧。冲突论认为,分化与整合是二元对立的两个部分,泾渭分明,相悖而行的两个过程。冲突主义者强调,在分化过程中,各部分、各等级之间产生强大的张力,促使个体、群体之间不和谐,充满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导致社会共同体的消解或不良整合。
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分化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分化为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注入了无限活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急剧变迁致使西北地区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故而强调社会结构变迁在西北民族地区诱发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从冲突学派的观点看,当前西北民族地区由社会结构变迁诱发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阶层结构的分化与贫富差距。改革开放前,西北地区的阶层结构比较单一,被概括为“两阶一层”(工人、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个人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不断拉大,阶层结构也出现了分化。
公平、适度的阶层分化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及社会需求,分配相应的工作岗位,以便每个人都能够为社会做出大小不等的贡献,获得与之相称的报酬,占据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社会所需要的岗位都有不同层次的个体来填充,并为个体留有通畅、公平的社会流动途径,只要努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此一来,社会功能和效率的发挥将会达到一个极大值。相反,公平缺失、过度分化的阶层结构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过度分化,即不同阶层在资源占有上极不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够公平,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过于狭小,社会底层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弱势群体看不到改善社会地位的希望,在心理上容易生发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常怀不满情绪,伺机以个体暴力或群体性事件等方式宣泄情绪。强势群体具有心理优越感,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品位,以便与中低层群体“区隔”,并对劣势群体采取偏见和歧视的态度。结果往往是,不同阶层的和谐关系难以为继,排斥、偏见和歧视等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
时下,西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都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而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西北地区收入阶层结构过度分化,分化机制公平缺失的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些都为西北地区的社会和谐埋下了隐患或风险,国内外反动势力常常利用“不公平”说辞及人们的“不满”情绪“大做文章”,煽动不法分子以极端行为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为什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社会财富无限增加的条件下,反而出现了个体、群体关系的不和谐呢?这是因为,社会分层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位置或资源优势,即主要强调“我比别人多多少或少多少”的问题,而非“我有多少”或“我比以前多多少”等问题,因此,总体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分层诱发的矛盾和问题。以下引述社会学家陆学艺和郑杭生的两段话来说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发展的悖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盛赞的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在社会发展领域却存在着许多令相当一部分群众不满意的问题,社会并非十分安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就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到了现在,则出现了‘领着低保金骂社会’、‘开着新买的轿车骂政府’的现象。”(陆学艺,2004)
“不仅利益受损者会产生或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剥夺感,而且即使受益者也会产生或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这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不同的个人、群体,有的受益,有的受损,而受益者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因受损程度高低而相互区别。”(郑杭生,2008)西北地区也不例外,如杨圣敏在新疆研究时发现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吉克人世代生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却始终保持着内部团结稳定、家庭和睦、尊老爱幼、无犯罪记录的道德社会的特点。而库车县虽然为全国西部百强县之一,2006 年农牧民人均收入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3倍,却始终存在较多的刑事案件和各种不安定事件 库车县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一部分人的被边缘化并因此而产生无助、失落、绝望甚至对社会的仇视 不患寡而患不均”(杨圣敏,2008)。
第二,民族分层与民族关系。历次普查数据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都显示,西北各民族之间在教育、职业地位、收入、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以下数据可供参考。
1997年,全国5800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近60 %(滕星和王军,2002)。2009年民族自治地方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3597万人)的543%,比上年(525%)上升18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比全国(36%)高128个百分点。按照新的贫困标准,2006~2009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45%、522%、525%和543%,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民族间、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但存在,而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李寅,2010)。
民族问题源于民族差异。差异无非是文化差异、生理差异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三种差异相互作用,在不同情境下有时相互强化,有时相互抵消。其中,社会地位差异是造成民族之间偏见与歧视、仇视与冲突的导火索(科普林,1997)。西北地区的民族分层,在一定条件下会影响各族人民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对居住格局、交友状况、族际通婚都有重要影响,甚至强化民族认同,以致民族之间重构、建构民族边界,影响人们对“他族”“他文化”的评价和态度。民族分层是族际和谐关系的潜在威胁,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市场化对效率的过分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有渐渐拉大的趋势。马戎先后两次在拉萨流动人口调查中发现,2005年汉族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是藏族流动人口的15倍,而2008年扩大至22倍,并指出藏、汉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收入上的分层是诱发“3 14”事件的社会因素之一(马戎,2009)。赵健君(2009)分析指出,“新疆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分化趋势,是引发‘7 5事件’和影响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利益分化与利益冲突。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人们的利益诉求必然发生分化,以至于利益分配方式和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个体与个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都在进行着利益的博弈或争夺,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普遍的矛盾和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发展。
第四,观念的嬗变与社会失范。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映,尤其是随着社会变迁及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西北各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趋于多元化和理性化,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其后果是,以共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传统和民俗文化将会不断流失、裂变,民俗文化的规范功能逐步式微,以致无法维持西北民族社会的正常秩序,新型的法理社会尚未成型,必然出现“道德真空”和“社会失范”现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