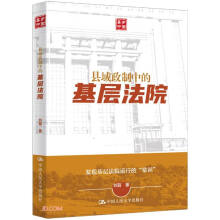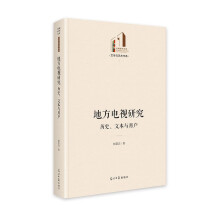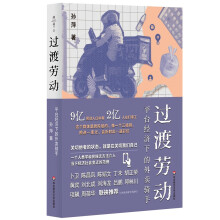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鳟或没有鲸,没有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日“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营造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