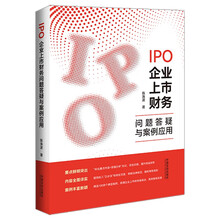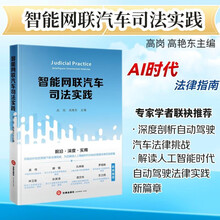《知识产权论(第二卷)》:
临摹是一种常见的艺术研习方法,它在著作权法上有一定的意义。《著作权法》第52条第1款曾经规定:“本法所称的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立法者在罗列了八种具体的形式后仍借助于一个“等”字来了结“复制”的含义,可见它有多么丰富的存在形态。
当然,不同的复制形式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就临摹与法律列举的其他几种相比较,可以看出,其他方式都是用机器设备来完成的,其中拓印的“机械化”程度虽然不太高,但基本上仍是非常被动地再现既有的作品,而临摹的特殊性则在于,它是完全“人工化”的,虽然临摹者模仿的是他人既有的作品,但是他仍然有一定的主动性,即他在临摹的过程中可能将自己的技能、理解融合到临摹的结果中去。甚至可以说,临摹者有时实际上会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对被临摹作品的篡改。但是,无论如何,临摹还是对原作品的一种再现,即使在再现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也是对原作的(实质上的)部分再现,也就是复制。有没有将原作糟蹋成面目全非的?也许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那种做法已经与临摹无缘了。
由于复制权专属于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故临摹也成了一种受到法律约束的行为。这会妨碍艺术学习和进步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著作权法中还设计有合理使用制度,它确保为了学习、教学、版本保存等目的可以自由、无偿地进行临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临摹在法律上的意义却变得模糊不清了。《著作权法》经过2001年10月的修订后,上述复制的定义被挪到了前面。新法的第10条第1款第5项规定:“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不难看出,“临摹”已经“蒸发”掉了,一点声息也不曾留下——笔者曾经试图找到立法者的一些书面解释,但是,一直不能如愿。(不过,从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第21页可以看出,直到1999年1月,《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对复制权的定义中还是列有“临摹”一词的。)
那么,后果是什么?也就是说,临摹还属于作者著作权所涵盖的行为么?如果单纯从复制权的定义来看,一两种使用方式没有列入定义并不妨碍将其理解到权利当中去,因为,如前所述,立法者采用了“等方式”一词,这表明被列举的方式只具有示例的性质,而没有穷尽实际存在的可能。因此,只要能够通过适当的解释,说明临摹与复制的内在联系,就仍然可以将其纳入复制权。换而言之,临摹的法律属性并没有因修法活动而产生变化。
但是,这种结论面临一种逻辑上的障碍。既然立法者原本在法律中列举了临摹,在修改法律时单单删除了它,却没有触及其他七种示例,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定义的行文结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立法者对它的认识生变了。
立法者可以改变自己的认识么?当然可以,而且他的认识一旦变化,全国的法官也要调整自己的立场。
然而,这个结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如果它成立,就意味着新法生效后临摹不再会涉及作者的权利,可以任意发生了(是否会触犯原作者的精神权利,另当别论)。可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0项却仍然保留原来的规定,称“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属于合理使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0月作出的关于著作权法的解释第18条第2款再次肯定了这一点(注意,在这项规定中“绘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临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