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中之重的制造业
现代经济应该具有非物质性,以及制造业在后工业时代无足轻重的说法,纯属是对基本现实的误读。
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1791
不计其数并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工业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也让人们感到压力重重,实际上,这还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情。在工业前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仅仅能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最富有者才会拥有单件生产或是小批量制造的高质量手工品。即便是当时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譬如砖、陶器或是最简单的纯金属物件,也会因为价格不菲而只能为极少数人所购买。而对于最贫穷的农民家庭来说,他们拥有的制造品就只限于几个饭锅和几件可怜巴巴的厨房用具,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张单人床,在以谷物为主食的社会里,每家还需要几个盛装粮食的容器,实际上,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依旧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步入工业社会最初的几十年里,城市新移民的全部财富也不过只有一件做工粗糙的火炉和几件简单的家具而已,且大多人也只有一件可换洗的衣服。对于物质文明的描绘和剖析,恐怕没有比《物质世界:一个全球家庭的写真》(Material World: A Global Family Portrait)一书更深刻、更贴切、也更有说服力的了。在这本书里,作为所在社会的典型代表,来自30个国家的家庭将全部财产陈列在他们的住所前,在这些家庭中,有些空空如也,有些财力充盈(Menzel,1994)。一组名为“成长”(Barber and Benson,2010)的系列摄影作品曾赢得皮克泰国际摄影大赛(Prix Pictet)的第三名,它从令人震撼的视角记述了贫富差距的力量。但是,最能体现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例证还是来自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该中心对美国人认为不可或缺的事物进行了民意调查。在这份必需品的名单中,1996~2006年增长比例最大的依次是微波炉(2006年,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生活中离不开微波炉,10年间增长了36%)、家用计算机、洗碗机、干衣机和家用空调(Taylor, Funk, and Clark,2006)。不过,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一切都经历了倒“U”型逆转:到2009年,上述商品的必要性程度均大大低于2006年(全部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Morin and Taylor,2009)。即便如此,仍有2/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干衣机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88%的人则认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
在以大生产商品作为社会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上,美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绝佳范例;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日渐富裕正在成为一件让美国人感到越来越压抑的事情。美国私人及政府囤积工业品的历史已有150年。在政府层面,我们想到的不应只限于联邦政府拥有的车辆、建筑物或是水坝,还应包括从间谍卫星、战斗机到航空母舰、核潜艇以及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各种军事武器。
在最初阶段,个人的实物性消费全部是为了改善生活标准(从电冰箱到电话,从电梯到疫苗,无一例外),不过,时至今日,人类的采购行为(精确地说是负债增加行为)却尽显奢侈浪费,但却品位全无,定制性法式豪宅、开悍马或民用型装甲车无疑就是这种趋势的极端体现。
而在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近期的炫耀性消费更是呈现井喷式增加。尽管这种消费模式还只局限于大都市的精英阶层,但这种消费的强度却让少数在总体上依旧处于极度贫困的国家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主流市场。至于成功的现代生活到底应如何定义,似乎已经毋庸置疑,那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工业品:尽管这些高档奢侈品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抱有奢望。因此,工业品的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听到人们说,后工业社会已经让工业沦为配角,因为强大的软件力量正在不断造就一个让链接、信息和知识超越于单纯物质的电子世界。客气地说,这种想法或许可以被称为误导;如果毫不客气地讲,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还有些人或许仍旧承认人类的物质需要,但却声称,后工业社会根本就没有必要制造任何东西,而且可以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工业产品。
几十年以来,全球化的倡导者始终在大声疾呼外包和国际贸易的好处,但这种安排本身就有其弊端(Bhagwati and Blinder,2009;Fletcher,2011)。将某些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的合理性绝不缺少例证,同样,证明对外贸易的可取性、有益性的示例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即便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如果抛开意识形态而无止境地追逐自由贸易,过度依赖进口或是不加选择地对整个工业实行外包,必将导致该经济体不断虚化和弱化。所谓制造业已不再重要,我们无需担心制造业的衰落,现代经济的繁荣源于服务,以及出口高附加值服务有助于确保进口工业品所需资金等种种言论,完全是无稽之谈。本章将阐述制造业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的典型地位。
工业化社会
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家庭里,很多财产是他们在生活中获得基本尊严的必要前提。床、盘子、刀具、杯子、鞋、肥皂和毛巾都属于这类物品。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会倍加珍惜隔热墙、保温好的门窗、坚固耐用的家具或火炉;天黑之后,功能齐全的厨房和整洁光明的灯具则成为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对那些通勤上下班的人来说,可靠的汽车(或自行车)、火车和地铁以及四通八达的公路是最基本的必需品。而构成物质消费的其他物品则属于可有可无的非必需品,如果认真对照一下这些非必需品,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当代北美家庭中觅得身影。
不过,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大部分财产则是居于两者之间,它们既非必需品,亦不代表任何富裕和奢华,但却会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舒适快乐。这类物品的范围更广,从小型家用电器到书籍,从花园用具到运动设施,从家具到复制音乐的小设备,形形色色,花样繁多。在传统社会中,尽管大多数人的主要时间花费在所处乡村或城市的狭小区域内,但大规模流动已日渐成为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商业事务或休假往往都需要进行长途旅行,而这就要求以同样的规模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原动机和各种运输工具的制造。
而这些物质需求则要涉及各种行业的制造业,它们要从世界各地获取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雇用数以亿计的工人,而且这样的工作永无止境,因为新产品总是层出不穷,不断取代陈旧或过时的老产品。考虑到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不计其数(目前全球能进行高端消费的人数约为15亿人,达到中等消费水平的人数约为20亿人),为此,制造业只能放弃它本身拉丁词根所代表的内容,即 “手工制作”。在今天的市场上,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物品由手工制作,高水平的机器化和自动化以及电动工具无处不在,让机器成为标准,也让人类可以凭借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手工制作”这个概念早已经成为陈年往事。
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消耗的食品。在传统的生存型社会中,农民种植农作物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消费对象往往是在地域遥远的市场,与此同时,随着肉类及乳品摄入量在比例上的提高,大部分农作物实际上仅用于家畜饲养,而非直接用于人类消费。这样的安排就需要大规模地生产人造化肥、杀虫剂以及除草剂等物品,以维持农作物的高产;为实现及时高效的耕种、栽培及收割,需要大批量地生产拖拉机、插秧机和联合收割机;为了将农产品从产地运送到距离遥远的市场,需要大量的卡车和货轮。由于这些农机农具的存在,地球才得以养活70亿人口,为近20亿人提供充裕的食品供给,并将全球营养不良者的数量减少到不足10亿人(Smil,2001,2011)。
其他生存必需品还包括家庭、工业所需要的能源供给,与能源供给相关的钻探设备、油泵、油气压缩机、油井套筒、输油管线、油罐和炼油厂,以及为提取、加工和输送石油天然气提供必要条件的煤矿、选煤厂、卡车、火车和大型货轮等。最终利用这些能源的工具则包括为大型发电涡轮机提供增压蒸汽的锅炉、炼炉和原动机: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能源转换方式,为货轮提供动力的大型柴油发动机是最有效的动力转换方式,而商用飞机发动机则是最可靠的动力系统(Smil,2010)。当然,发挥这种最终用途的最大一个类别还是机器设备、工器具以及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动能和电磁能的光电设施。
或许还可以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两个端点,出生和死亡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种种事物:床单、手套、听诊器、注射器、药品,以及绘制每个衰老者心跳直至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心率监视器。在一个多数人脱离“制作东西”这个人类基本活动的社会里,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还是有必要重申: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现为我们对形形色色有形产品的依赖,也就是说,通过熔化、精化提炼、化学反应、分离以及合成等手段,首先将原材料首先转化为各种中间品,这些中间产品五花八门,从金属到塑料,从木材到面粉,几乎面面俱到,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工,形成最终产品并通过装配获得可交换的物品。
上述定义只是采用了接近于官方对生产性活动的定义,而没有使用一个还不算理想的术语:制造业。美国统计局将制造业定义为这样一个行业门类:“通过一系列的机械、物理或化学过程,将材料、物质或零部件转换为新产品的生产部门。对于工业品零部件的组装,除应归属于‘第23节,建筑业’以外的活动也被视为制造业。”(USBC,2010)这个官方定义将制造业描绘为:
以动力驱动机器及材料加工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厂、设施、加工厂等制造型生产机构,这就涉及制造性活动具有机器和人类两个要素兼具的特征。此外,个人或家庭作坊以手工方式将材料或物质转化为新产品的活动,以及面包房、糖果店和零售店等直接向普通大众出售上述产品的个人或家庭,也被纳入到制造业的范畴。
这个定义确实有点含混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是它的内涵和界限。事实上,所有现代制造业还要涉及管理、薪酬和会计等问题,而且它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设计创新、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载体实现零部件的即时运输。一项国际对比性研究显示,2005年,美国制造商向外部公司采购的服务额约占全国工业品价值增值量的30%,在欧美主要成员国,这个比例在23%~29%之间。另一项研究则表明,2008年,在制造业领域,与服务相关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制造业总就业人口的53%,德国、法国和英国在44%~50%之间,日本为32%(Levinson,2012)。因此,对于美国的制造商而言,他们在实际生产运营部门吸纳的就业量略低于服务性部门吸纳的总就业量。
尽管现代工程创造的很多产品在表面上依旧没有摆脱其鼻祖,但现代产品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是由一系列零部件和服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汽车就是这种巨变的典型示范:尽管它们依旧是复杂的机械构造物(目前的汽车大约由3万个零部件构成),但是到了现代,从发动机运行到气囊配置等各种功能则全部由计算机控制实现,而它们所需要的软件甚至比战斗机或喷气式客机的操纵软件更复杂(Charette,2009)。1977年,通用汽车第一次在“奥兹莫尔比”汽车上配置了电子控制设备(ECU),今天,即便是最便宜的汽车也要配备30~50个电控设备,而这又需要1 000万条指令代码,而高档豪华汽车配置的70~100个电控设备则需要近1亿条指令代码,相比之下,操纵波音787航空电子设备和机上支持系统的代码却只有650万条,美国空军的F-35战斗机的指令代码更是只有570万条。
今天,电子元器件及软件在高档汽车成本中占据的比例高达40%,仅软件开发本身的成本即高达15%,换句话说,每条指令代码的成本为10美元,这意味着,一款新型汽车正式出厂之前的投入成本大约为10亿美元。汽车早已经演化为一种离不开复杂软件的机电结合体。正因为这样,乔治·塔西(Tassey,2010)才认为,我们应该把制造业看做一种价值流,而不是战略,但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采用的操作性定义和数据收集过程却无法反映这些复杂的现实。
对于由制造型企业提供的这些关联性服务,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将其划分为“附属性”业务,属于制造性活动。但“如果由单独的机构提供服务,且服务为该机构的主营业务,那么NAICS则不再将该机构划分为制造业”(NAICS,2008)。目前,不管规模大小,很多制造型企业均大量采取了外包策略,不仅涉及市场调研和薪酬管理,甚至还包括产品的设计和研发(MacPherson and Vanchan,2010),以至于它已成为价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还不止于此:将制造业定义为将材料转换为新产品的核心,在于如何定义何为“新”,而这就有赖于对边界的主观设定。
实际上,NAICS就是一系列可被视为提供新产品的活动,从牛奶的瓶装和灭菌,海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到服装批发、印刷或预制混凝土生产,再到电镀、机器零部件的改制和轮胎翻新,皆包括在内。尽管这个目录中未包含伐木和农业似乎并不意外,但NAICS确实也漏掉了很多理应被纳入制造业的活动,譬如选矿(被归入矿业),在建设工地现场进行的建筑装配(归入建筑业),零担货物及小批量分销(归入批发业)以及金属定制切割和计算机定制组装(归入零售贸易),而出版以及出版和印刷的兼营活动(归入信息类)则因“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体现为其信息内容,而非产品的分发格式(即书籍或软件存储体)”,而没有被划入制造业(USBC,2010)。
毫无疑问,上述事实表明,对制造业作出更符合现实、客观且更具包容性的定义不仅具有统计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考量整个门类的真实绩效,为制定行业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van Opstal,2010)。此外,考察这两个行业产量的方法也存在差异。制造业的产量是一个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它对外部的采购价值,或是等于该部门的销售额减去购买原材料、中间材料和能源的价值。即便是在某些服务(如会计和设计),甚至是实际生产由零售商而不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情况下,依旧采取这种计算方法。相比之下,商品产值则等于国内生产产品的支出与全部商品进口额之和,再扣除生产出口商品的成本。
这些方法显然是不一致的,对于后者,商品产值的核算不仅包括进口商品的零售成本(被扣除进口额的总和是指对外国产品生产及运输支付的成本,而非购买价格),还包含国内运输、营销及运行的融资成本。查尔斯·斯坦德尔(Steindel,2004)发现,相对于制造业产量,美国的商品产值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增长状态。他认为,这种令人费解的分歧源于如下三个原因:进口商品份额的持续增加,商品销售额中服务成分的提高,以及服务要素在消费品出厂后营销过程中的比例相对于资本品价值的提高。
上述因素均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会让我们将制造业局限于一个抱残守缺的定义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现代制造业已高度机械化,甚至可以说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个事实,也丝毫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及程控设备目前已运用于制造业的每一个阶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概莫能外。其次,在定量评价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占有的权重时,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对制造业边界的人为限定,但这种内涵上的缺陷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制造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在大型制造商在对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进行外包或分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持续增长的研发、高品质专用零部件的加工、定制化组装、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目前已普遍实行在线运行),现代制造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这种现象还会因“原产地”概念而显得越来越弱不禁风。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机器设备也可能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而制造这些零部件的材料和元件同样有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因此,任何试图指定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如果按目前的通行做法,将原产地指定为完成最终组装工序所在的国家,这就会人为扩大该国的出口额。2009年,安德鲁·拉斯维勒对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物料清单进行的分解,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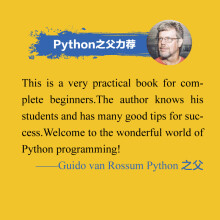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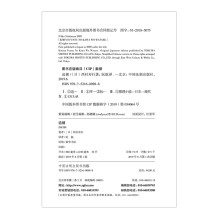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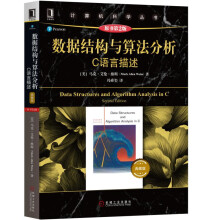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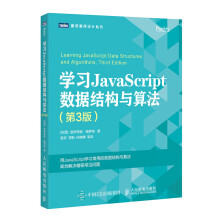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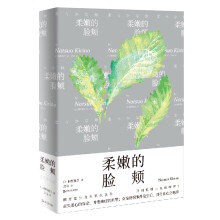

★除了瓦科拉夫·斯米尔,没有其他人的书令我如此期待。他以自己大量丰富的科学和能源知识、历史和商业知识,对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和主题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比尔·盖茨
★这是一部现代世界无可替代的、瓦科拉夫式的著作。假如有人想知道,在数字时代制造“东西”为什么还如此重要,那么,看看这本书,你就会豁然开朗。美国能否继续成为世界储蓄货币很可能要依赖于制造业的兴衰。
——迈克尔·切巴莱斯特(Michael Cembalest),摩根大通资产管理部首席投资官
★瓦科拉夫·斯米尔绝对是当代极具洞察力、目光犀利而且多产的历史、技术发展、人文及工业分析家。斯米尔的每一本书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引发深刻的思考,但恐怕没有一本书比《美国制造》来得更及时、更有现实意义。斯米尔以清晰的脉络和迷人的笔触将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和现状呈现在我们眼前,引人入胜、清晰且有条理,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并应该成为讨论美国未来发展的起点。
——马克 P. 米尔斯 (Mark P. Mills),曼哈顿学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