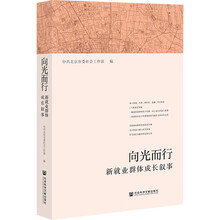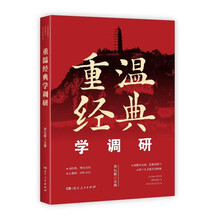从本质上看,宅基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的范畴,两者不能相互兼容。立法一方面承认宅基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而另一方面又对这种用益物权设置了一些强制性规定的原因,实际上是基于宅基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考虑。户籍与宅基地使用权分离,实际上是承认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持有不以户籍为前提。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物权的取得。物权取得的理论和立法都不能为以户籍为基础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提供充分的支持。户籍成为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决定性因素,是作为社会管理方式的户籍制度被过度适用的结果。农村居民转户后,仍然享有保留其原来已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上建筑物的权利,使得这些权利的物权性得以体现和彰显,而不是因户籍的变更而丧失或被剥夺。进一步说,农村居民户籍变更后,无论其是否继续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居住和生活,其原享有的权利并不因户籍变更而消灭。
户籍变更后,无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宅基地及宅基地上建筑物的权利,都不因户籍的变更而消灭。户籍不再是地权的基础,而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或公共管理职能的一种手段。户籍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原户籍持有人身份或职业的必然改变。原户籍持有人变更户籍后所从事的职业.既可以是原来的职业,也可以去从事工商业,还可以兼业。持有城镇居民户籍,不影响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户籍不构成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阻却事由。如果一方面鼓励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又对土地流转的受让人的身份加以限制,又推又拉地倡导土地流转,其结果只能是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并可能成为土地流转中的一方当事人。
扩大土地流转中的融资和信贷,也需要通过户籍与地权的分离来支持。农村土地市场缺乏融资功能的一个原因是土地交易当事人的身份受到限制,土地流转的封闭性使得土地几乎不可能成为融资手段。一些禁止性法律规则不支持以土地融资,如不得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抵押,也不得以宅基地使用权作抵押,它们表面上是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实质上是维护土地流转的封闭性,而土地流转的封闭性因缺乏市场配置资源的因素,其结果要么是使市场交易意义上的土地流转成为不可能,要么是为通过行政力量配置市场要素提供可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