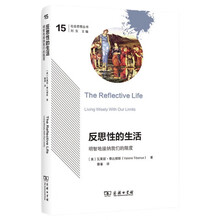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近思与远虑》:
“准此,主体便知道,它自己只不过是意志,而不是知识。因为,尽管自我(ego)作为所有表象的必要关联物而制约着它们,它本身却从未成为表象或客体……”①
叔本华的这篇论文是从1813年6月开始撰写的。也就是说,他是在1811年9月于柏林大学听了费希特的课以后不到两年就动手写了(而且写得与后者的思想如此相似)。但我们只能把话点到这儿,不能再作进一步的推论了,因为若想达到这种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意志本体论,除了受费希特的影响以外,叔本华确实还有其他的路好走。比如说,他可以独立沿着康德的思路去寻找一个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先验统觉”,他也可以顺着充足理由律的四种形式去上溯那个给予一切理性关系以充足理由的最后的“根”,②他又可以因为自己“英国哲学家”式的治学风格而直接从对人们心理现象的观察中找到这种类似于弗洛伊德式的结论,同时,他更可能因其亨利希的遗传而直接从自省中谛听到那蕴藏于灵魂最深处的生命冲动的脉跳……
但这一切都无关宏旨。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般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更使人感受到那个作为人之形而上本体的意志在近代精神中正呼之欲出!这种思想,在今天的哲学界中已如此深入人心,似乎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愿意去反对一种认为主体的生命冲动的意志本原乃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出发点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又总是和作为意志哲学开山鼻祖的叔本华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在纯哲学的思辨中,哪怕一丁点儿真正的建树都是极端困难的,那我们就可以借叔本华所带来的观念变革去判定他在全部哲学史中的地位了。
让我们的分析再接着往下走。我们已经说过,费希特的哲学是兜了一个圈子的:为了保证他的“自我”不至于在恶无限中永无止境地成为有限,他先在其体系开端设定了“自我”,让它自己设定自己,以便自己回归于自己。而乍一看,叔本华的体系似乎也与此相似:整个世界的意志本体诞生出了作为意志的主体,它由此好像也应该能够在逻辑上保障人类生命冲动的命运。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近似而已。由于叔本华哲学体系上的粗糙,由于他的思路上潜伏着一个我说过的那种逻辑断点,那种高居于其体系顶端的神的意志或者奥古斯丁式的意志(必然),和作为那种宇宙本体之派生物的人的意志或者休谟式的意志(自由),本来就全然是两码事。所以,在叔本华的体系中设定主体生命冲动的宇宙生命冲动,不仅不能保障前者的命运,反而足以将其窒息。
这正是叔本华哲学中的一个难解的关节点。很多研究叔本华的学者都对此大惑不解。比如罗素就说:“我们也许料想叔本华要把他的宇宙意志和神说成是一个,倡导一种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学说不无相像的泛神论学说,在这种学说里所谓德性就在于依从神的意志。但是在这里,他的悲观主义导向另一种发展。宇宙意志是邪恶的;意志统统是邪恶的,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全部永无止境的苦难的源泉。”①然而,罗素就没有想到,叔本华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来乃是与斯宾诺莎的哲学不类的。在斯宾诺莎那里,只有一个东西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那就是作为泛神论上帝的实体(必然),而从属于它的所谓人的自由,不过是对这种必然的认识和皈依。而在叔本华这里,问题显然就大不相同:他一方面同样设定了类乎斯宾诺莎之泛神论上帝的意志本体(必然),另一方面却又设定了主体的形而上本质——意志(自由)。这种主体的无意识生命冲动由于从一开始就径直是一种原发动力,遂同样也是一条射线的端点,同样不能被任何东西所决定。由此,叔本华的哲学体系就绝不能凭靠对外部必然的认识而融为一个整体:它注定了达不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只能限人人神冲突的困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