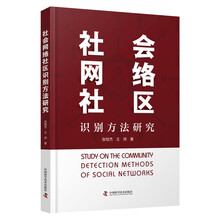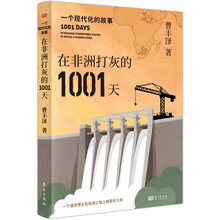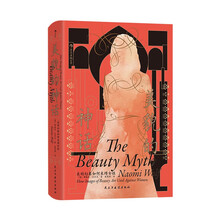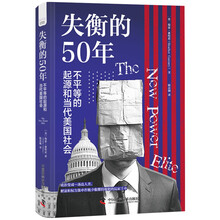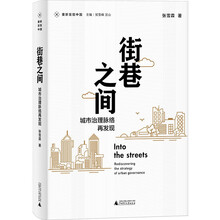一、关于布鲁尔及其“强纲领”
(一)作为爱丁堡学派“理论家”的大卫•布鲁尔
就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崛起的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而言,大卫•布鲁尔是与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齐名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他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理论已经成为这个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就这个学派的构成人员各自的特点及其理论贡献而言,布鲁尔和巴恩斯堪称其中的“理论家”,而拉图尔( Bruno Latour)与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则可以被称为其中的“实践家”(当然,这样的称呼是就他们的研究特色和理论成果的特点而言,并不是说前者仅仅涉及理论,而后者仅仅进行实证性的经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界于这两者之间的人物。显然,就了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成就而言,布鲁尔在本书中提出的“强纲领”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大卫•布鲁尔是当代著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他于1942年出生在位于英国中部工业区的德比,曾经在基勒(Keele)大学受教育,于1964年获得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学位。之后,他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在两年之后即1966年,完成了实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1967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的讲师,从而与巴恩斯一起成为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元老级人物。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即《知识和社会意象》,于1976年首次出版(后于1991年出了第二版,除了原有内容基本保持不变、只修改了几处文字错误以外,主要增加了“第二版前言”和“后记”,以之作为他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的回应)。
接着,他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立场出发,结合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的社会哲学维度的研究,先后于1983年和1997年出版了两部有关著作:《维特根斯坦:关于知识的社会理论》和《维特根斯坦:规则和制度》。另外,在此期间,他还与他的两位同事——巴里•巴恩斯和约翰•亨利(John Henry) ——合写了《科学:社会学分析》,作为研究院教材于1996年出版。1998年,布鲁尔被任命为科学社会学教席的专职教授(personal chair),并且成为美国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维也纳科技大学、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以及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客座教授或者客座研究员。此处材料主要来自大卫•布鲁尔于2000年5月19日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就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的传播状况而言,可以说它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洲已经基本上“遍地开花”,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因而“水涨船高”,布鲁尔的上述三部主要著作,尤其是《知识和社会意象》,也因此成了人们广泛注意、研究和批评的焦点,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
囿于篇幅,这里不打算一一叙述和评价这部著作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尔这部著作虽然篇幅并不很大,但是人们读了本书就可以切身感受到,他以“强纲领”为中心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也正是因为如此,要进行这样的叙述和评价,我们就至少需要写一部与这部著作篇幅相同的著作),而只能集中考察和论述它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强纲领”和与知识成因有关的相对主义。在我看来,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面共同构成了《知识和社会意象》这部著作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个学派的理论核心。所以,我们试图以此举达到“纲举目张”之效——至于实际结果究竟如何,就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当然,《知识和社会意象》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也都必须由读者来评价,包括作者、译者、出版者在内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越俎代庖”。
(二)“强纲领”及其相对主义倾向
对于国内初次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著述的读者来说,他们对“强纲领”是什么颇有些摸不着头脑——“纲领”尚可理解,加上一个“强”字又作何解呢?其实,这主要是由于对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有关的学术背景还不甚了解。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核心是“强纲领”,主要理论取向是对科学知识成因进行社会学说明——在这里,所谓“社会学说明”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学理性说明,但是与传统的理性主义所认为的“学理性说明”相比,这种说明在客观性、确定性、精确性、可重复性方面都要“大打折扣”;这也就是说,无论与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精确科学相比,还是与不断追求量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的经济学相比,“社会学说明”在这些方面都相差甚远——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立场是传统的理性主义所坚持的立场。
另一方面,进行这样的说明通常都必然涉及科学史,亦即利用科学史上的材料,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角度来说明科学知识成因——这基本上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崛起以前,人们在进行这个方面研究时所采取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纲领”要求的做法,同时,这种“纲领”还要求,只有当不涉及某些社会因素就无法对科学史上的某个阶段加以全面说明的时候,人们才应当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因此,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前,人们在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角度对科学知识成因的研究和说明过程中,对社会因素的态度基本上是“能避开时则避开,不得已时再求助之”——他们基本上是同等看待这些社会因素与不合理性的因素的。与这种态度相比,爱丁堡学派所坚持的基本态度则要“强硬”得多。他们认为,各种社会因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对于知识的形成过程来说)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参见詹姆斯•罗伯特•布朗(James Robert Brown):《引论:社会学转向》(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Turn),见《科学的合理性:社会学转向》(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Dordrecht,1984,p3。正是这种基本态度所具有的更加“强硬”的特征,使爱丁堡学派体现这种态度的纲领被学术界称为“强纲领”,而且他们自己也完全接受这种称呼。
那么,“强纲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体现爱丁堡学派在研究知识成因过程中所论述的相对主义的呢?
具体说来,大卫•布鲁尔在本书中提到了它的四个“信条”参见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econd Edition,1991,p7;也可以参见英文原书第7页(本书边码)。笔者在这里并没有逐字逐句地引用布鲁尔的原话,是为了简明扼要地进行概括。:
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 beliefs)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
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
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
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反身性)。
布鲁尔和爱丁堡学派其他成员坚持的就是由以上四个信条组成的“强纲领”。概括地说,“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正因为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才提出了上述四个信条,以之作为对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因的要求。
在这里,“因果性信条”所规定的实际上是对于进行这种研究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想研究知识的社会成因,就必须从因果关系角度出发,去研究究竟是哪些条件使人们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识;在此基础上,“无偏见性信条”要求研究者必须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绝不能因为谬误、不合理性、失败令人反感或者令人失望,就不去客观公正地对待它们;“对称性信条”则说明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无论就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而言,还是对于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来说,它们的社会成因都是相同的,所以当人们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因时,必须运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最后,“反身性信条”使研究者所坚持和运用的理论本身也变成了他自己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这种研究者必须把他用于说明其他知识和理论的模式同样用于对待和研究他自己的理论,从而真正达到对知识的社会成因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说明。
我认为,“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它坚持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东西。就这种观点而言,它不仅像以往的相对主义观点那样强调知识的形式(概念、范畴、表达方式乃至学说体系)的相对性,还进一步通过强调一切知识都是基于社会意象的信念,而且这些社会意象和信念又由于社会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主张对知识的内容进行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说明——就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而言,这种倾向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倾向。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从认为某种理论“是由社会决定的”观点出发,并不一定能够得出这样的观点不是相对主义观点的结论。因为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19世纪下半叶欧洲进行的“科学方法论大辩论”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领域”和“历史领域”一直是作为由独一无二、变动不居的事件组成的领域而存在的;因此,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说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决定的”,大致相当于说它并没有得到传统的理性主义所说的那种具有终极确定性的“决定”,因而,这种说法所指称的观点仍然具有非常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所以,无论是当前西方学术界其他学术流派成员,还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理论家们自己,都不讳言“强纲领”是相对主义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强纲领”乃至“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所具有的相对主义倾向呢?这种倾向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的功过得失有什么关系?我们又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