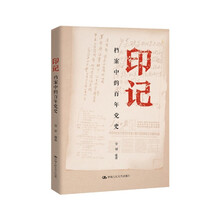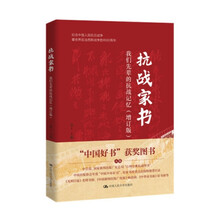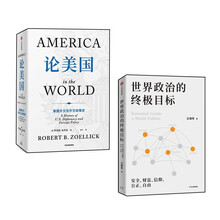艾云的笔力游走在这些女人的床榻、阴冷寒夜、疾患、病痛、容颜溃散、情感戏剧这些私人风暴的发生现场,将她们从历史恩宠与荣耀的虚广怀抱之中解救出来,去观察精神高蹈的低空盘旋,在肉身重力贴近地面的时候,如何席卷、拖拽并粉碎飞翔的倾向,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超越如何成为可能。
搁置形而上的根据,关闭朝向历史正门的迎奉论调,艾云在这些女人传记资料的裂缝间,以仁慈悲悯之心去探究她们的背影所泄露的秘密。如果圣徒的眼泪润泽世间百合的绽放,那么个人的献祭被当做永恒的证据呈现在神祗之前,也是基督教有关永恒的精纯记忆。精神标本不关心肉身的潮起潮落,标本抽干了生命体自身的行为机制,直接面对肉身的有限性,而不是将其作为中介推到思想者的面前,这是现代以后的事情。
当我们为罗莎·卢森堡圣洁、出众的判断力,以及在历史激流中思索的强悍理智所折服的时候,艾云的理解却是极度肉身化的,她说出了一个我们不愿也不忍去碰触的理由:她说罗莎的沉稳来自其行走的缓慢,她必须缓慢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因为她患有先天的髋关节脱位。无疑,这样思考加深了我们处理经验的难度,罗莎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领袖,她是列宁所称赞的翱翔之鹰,这就够了。她越是出类拔萃,就越有理由为无数个体的无聊、混乱、浅陋与怯懦免除道德责任,因为有罗莎代替众人走向革命祭坛,这也许是历史叙事的吊诡之处。
恰当的思考究竟源自何处,尤其时过境迁,我们只需领受思想者的结论,就以为获得了一种精神训练,即能够站在历史处境之外评头论足。罗莎曾说:是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侵犯我的自由感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了。于是崇高就获得了一个道德本能的根据,在这个天然的起点上,权力意志与求知意志都无法解释这个独特的女人,因为她说的是感受,任何生硬的知识理解都无抵临“这个个人”的感受性真理。换句话说,真理必须和感受在一起,世俗政治才可免于被意识形态绑架。除了笛卡尔式的严格推论之外,这感受已经表明,接近真理的喜悦与神启的至福存在某种秘密的通道,而现代政治实践的严格含义必然隐藏着神学因素,而不是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神圣彻底地遗弃了现代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