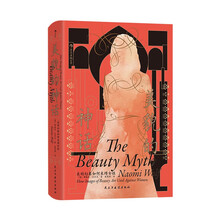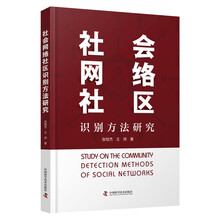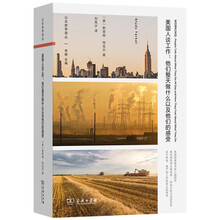剪不断理还乱的艺术边界
为什么艺术界时常发生艺术边界的争议?为什么艺术边界的问题总是争论而毫无结果?为什么人们对艺术边界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
大约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艺术定义或艺术边界的问题热议不断,提出的解决方案林林总总,却莫衷一是,常常是各说各的理,离达成共识尚相去甚远。也许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其中,进入了艺术边界论争的大合唱。美学家亦有人钟情于为艺术划边界,丹托可能是其中最大牌的一个。他先是提出“艺术界”理论,后又紧跟着“艺术终结论”,再后来是“艺术终结之后”,晚近警告说“美的滥用”。 好在艺术并不像丹托所划定的那样,他说他的,艺术走自己的。不过,艺术界的争论是一种复调,但声音却并不和谐,有些声音还挺刺耳。每隔几年,艺术界一有风吹草动,便有人拿“边界”来说事。此一情景可模仿马克思的传神说法:“一个幽灵,一个艺术边界的幽灵,在艺术界和美学界徘徊。”
本文并不想提出什么新的艺术边界的假设,而是想清理一下此问题如何被建构,又为何难以解决,简言之,换个角度来思考剪不断理还乱的艺术边界问题。
现代性的分化与艺术自立
稍有艺术史和美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率先出现在西方国家,据说文艺复兴之后已初见端倪了,到了启蒙运动时渐趋成型。与艺术边界问题密切相关的两件事不能不提,一是1746年有位法国神父巴托写了一篇题为《归于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把艺术分成三种:美的艺术、实用艺术、机械艺术。美的艺术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情感愉悦,它少得可怜,只有区区五种: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和舞蹈。 二是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哲学应建立一门美学学科,旨在研究人的感性经验,而最集中体现这一经验的是美的经验,而美的经验就是艺术的经验。 于是,美学一开始就作为艺术哲学而被确立起来。法国人说有一类艺术可以称之为“美的艺术”,其功能和目的都不同于机械的和实用的艺术;德国人则断言要有一个专门研究艺术在哲学分支,它不同于逻辑性、伦理学等其他哲学分支。两者可谓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今天听起来都是常识,但当时却有极其重要的开天辟地功能,为一片混沌的艺术和关于艺术的知识划定边界。
关于这两件事,我以为有些关节点需特别留意。其一是时间节点,两件事同时出现在18世纪中叶,正值西方启蒙运动高潮时期。其二,两件事都发生在西方,因为现代性率先出现在西方。所以,历史地看,艺术边界的问题也是率先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来,晚近才在中国语境中被讨论。其三,这两个事件也许没有谁影响谁直接关系,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这倒是提醒我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个有关艺术边界的事件呢?其中一定有某种内在关系。对三点的思考,都指向了现代性这个核心问题。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想想那时的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真的让人敬仰。他们个个抱负远大,关心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种种激动人心的宏大叙事。那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约是康德在1784年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大声喊出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启蒙哲学家、思想家及刚获得合法头衔的美学家们想做些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个个都有强烈的“边界意识”,要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知识领域划出界限。从自然科学到古典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及。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可以说是这样冲动的典范。在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划界运动中,少不了要给美的艺术定位,给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和舞蹈划界,给哲学划界,给美学划界……,在一个知识和观念经历巨大转变的时期,搞清一切边界,乃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思想冲动。
划清边界,也就是区分不同的事物、知识、对象,其实这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到了20世纪初,韦伯用更加冷静和客观的口气说到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乃是一个不断分化(或区分)的过程。最重要的区分是宗教的和世俗的东西分离,只此世俗社会和科学知识才得以形成。倘若没有这个分化,艺术仍旧卑躬屈膝地处于宗教伦理的宰制之下,决无什么美的艺术之蓬勃发展。由于宗教和世俗的区分,导致了一系列更多领域的细分,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价值领域的分化”。他特别指出了五个价值领域的区分: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智识五个领域在过去是彼此不分家,现代性则像是一个催化剂使之各奔东西了。韦伯注意到,审美(艺术)脱离了宗教教义和兄弟伦理的束缚后,开始注重艺术形式和感性表现,原先在宗教伦理的高压下,艺术家即使有这样的冲动也被宗教的力量给压抑了。只有当宗教的、道德的标准不再适合于艺术,艺术理直气壮地按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时,艺术的潜能才被激发出来。 我以为,艺术的自身合法化乃是艺术从现代性那里得到的最大奖赏!否则我们今天不可能讨论什么艺术的边界问题。
形象地说,现代性的分化就把世界区分为不同的区域,把人类活动区分为不同价值领域,把美的艺术区分为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和舞蹈不同类型。这样,在一个原本不加区分且无限广延和开放的人类生活世界里,就区分出特定的区域,界划出各自的边界。它们彼此不同,各有各的游戏规则而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不妨设想,“美的艺术”就是其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其中又包含了音乐、绘画等五个小公国。经过这样的区分,艺术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地盘耕耘,而美学家也守土有责地在自己的空间里思考。
如果说美的艺术与实用的和机械的艺术区分还只是艺术领域的分化的话,那么,背后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分化在悄然发生。那就是真、善、美的区分。虽说艺术从来被看作是真、善、美的统一,美学的理想也必以三者统一为旨归,但现代性的实际进程却使三者分离。此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这样!道理很简单,艺术要获得自己存在的权利和合法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存在根据和价值判断标准,因此与真、善分离在所难免。回到康德,他在大声吁请人们摆脱人的不成熟状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此时他雄心勃勃地建构了宏大的三大批判体系。这三大批判体系究竟是啥意思呢?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 那么,康德是如何阐述启蒙运动的呢?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一语中的:康德的贡献是把心理活动区分为思想、意志和情感三种形式,通过理性批判来检验认识原则、伦理原则和情感原则。康德学说的理论、实践、审美三大部分,构成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批判。 美学就是判断力批判,关乎审美活动中的情感问题,它有别于其他两大批判,有其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尽管三大批判关系密切,但从知识根基上说,他们各有各的问题和价值评判标准。韦伯以后,哈贝马斯从新的高度更加明晰地阐述了真、善、美分家,并在此指认这一重要的分化就是现代性的征兆:
韦伯认为,文化现代性的特征是,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由于统一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瓦解了,这些领域逐渐被区分开来。18世纪以降,古老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被安排在有效性的各个特殊层面上,这些层面是:真理、规范性的正义、本真性和美、它们因此而被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和道德问题或趣味问题。科学话语,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依次被体制化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和文化的职业相对应,其中专家们所关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这种专业化地对待文化传统彰显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它们分别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
在这一著名的陈述中,哈贝马斯指出了真、善、美各有其“理性结构”,各有其特定的核心观念和问题。更重要的是,分化所导致的体制化以及专业化地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艺术边界的基本语境。一方面是价值领域或真、善、美的区分,艺术作为以美为根据的人类文化活动,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评价标准;另一方面,相应的社会制度、专家及其专业知识建构起来了,美学的出现不过是这一制度化的必然结果之一。一方面是艺术家在不断地拓展艺术的疆界,另一方面是美学家不断地清理和论证艺术的边界。康德以后,黑格尔直接把美学界定为艺术哲学,而美学家几乎都把自己定位成艺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基本问题就是为艺术的发展和存在提供学理上的根据,通过艺术独立存在的必要论证。
说到这里,得出一个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美的)艺术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分化使艺术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价值领域而出现。真、善、美的区分既为艺术的自主性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又为艺术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现代主义与艺术自主性
现代艺术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现代主义的诞生。现代主义艺术是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激变。从19世纪50年代起至20世纪50年代,现代主义一百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西方艺术的地形图。就绘画而言,从马奈始,平面化改变了西方绘画文艺复兴以来所恪守的透视原则,印象派有力地颠覆了古典绘画色调而解放了色彩,立体主义动摇了牛顿式的三维空间及其视觉呈现,表现主义凸显出艺术家情绪和形式的新型关系,超现实主义以梦幻入画,达达主义无所禁忌地表现,抽象主义更是把画什么变成了不画什么,绘画艺术的任何规范和原则都不复存在。只要看一下马列维奇的抽象绘画《黑方块》,就会明白现代主义绘画有多大的颠覆性!这似乎是在应验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关于现代性特征的著名判断:“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马克思的判断不啻是现代艺术的真实写照!要注意的是,极尽新奇之能事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宗教和世俗未加区分的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现代主义艺术家摆脱了其他社会价值和体制的束缚、限制和强暴之后才有可能。所以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强调现代主义三个冲动之首是艺术和道德的分治,其他两条是依次是对创新和实验的推崇,把自我奉为文化的准绳。 毫无疑问,第一条是现代性的分化之体现,也是后两条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而后两条创新实验和自我崇拜则是现代主义的动因。只有当艺术与非艺术边界清晰截然分开,“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才有可能出现。所以王尔德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19世纪下半叶登场了。他的人生经历简直就是一个艺术的生存方式,其座右铭是:“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正是因为艺术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他断言在画家描绘伦敦的雾之前,伦敦人令人悲哀地视而不见,是画家教会了伦敦人欣赏伦敦的雾。这大概说的就是印象派画家莫奈所画的多幅伦敦雾景画。这么来看,唯美主义的主张就有其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批判性了。艺术不但和非艺术的生活泾渭分明,更重要的是艺术乃是生活的典范,而生活是平庸、乏味的,充满了无趣的、刻板的陈见。恰恰是艺术提供了生活中所没有的东西——美。美并不在生活中,美只存在于艺术世界。王尔德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唯美主义三原则:第一,“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第二,“一切坏的艺术都是返归生活和自然造成的。”第三,“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艺术不再模仿生活最典型的形态大约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在波洛克的绘画中彻底消失了。彩色的斑点和流淌的色线构成了画面,既无视觉焦点,又无熟悉的物象,除了有些标题的暗示性之外,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绘画中被彻底过滤掉了。关于现代主义绘画的这种走向,格林伯格有精彩论断,他认为这是康德之后艺术的现代性自我批判的必然结果。传统绘画画什么或让观众看到什么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造型艺术原理,现在的画家不要观众看到画了什么,而要他看到“画自身”。只有当画什么也不画的时候,“画自身”才能出现,那就是画的媒介,就是色彩、线条和形状。 格林伯格的经典看法从造型艺术角度阐释了现代艺术的边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这里,我们瞥见现代主义艺术对于艺术边界确立的积极作用。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现代主义美学的核心观念——艺术自主性(autonomy)。自主性就是自身合法化的,艺术的价值判断和存在的根据不在艺术之外,而在艺术自身。所以真和善的价值标准都不再适合于艺术。艺术的唯一标准是它自身的美,所以它才被称之为“美的艺术”。它与任何有实用功能和目的的“艺术”都有所不同。自主性是现代艺术安身立命的根基,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从以上分析在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强了艺术的自主性。自主性是艺术边界学理上成立的依据。
但是,现代主义又有另一面,即当它要摆脱宗教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影响时,就深深地依赖于艺术的自主性,可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它便在其庇护下恣肆狂放地生长,最终又危及艺术的自主性。回到贝尔关于现代主义动因的三点概括,摆脱道德束缚的艺术已经彻底自由了,创新实验和自我崇拜也就无所顾忌地膨胀起来,好比风筝解脱了绳索的牵制而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凡事没了限制就必有相反的可能,现代艺术正是这样。以形形色色先锋派或激进面目出现的现代主义艺术,在高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时,暗中潜藏摧毁自身的反冲动——反艺术。反艺术是从艺术自主性那里得到合法性的,但反艺术的出现又反过来反对艺术自身。其结果必然是对艺术本身充满的敌意,是人类文明的反目仇视。现代主义艺术的这一危机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被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所预见到,他发现形形色色的“新艺术”来者不善,它们采用一种“去人化”的策略来表征,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从艺术中被驱逐了,剩下的是充满怪诞不解之物的艺术世界。这种艺术的命运是对文明的敌视,对传统的颠覆,最终是艺术自身的瓦解。
我们看到,如果说从印象派开始的现代主义绘画还只是在架上画的小天地里折腾的话,那么,创新和自我标榜的无限冲动便会重出藩篱,冲破一切可能束缚创新和自我呈现的桎梏。各种极端的艺术实验在所难免。当杜尚把男厕所的小便斗拿去展出时,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在我看来,与其说《泉》有什么价值和看点的话,不如说它的重要性不在他自身,而在于向王尔德以来的种种艺术价值、规范、观念、惯例挑战,也即对艺术边界的挑战!也许在他看来,必须以一个完全和艺术不沾边的现成物来颠覆艺术既有的边界,必须以极度陌生化甚至令人震惊的方式,才有可能把现代性所确立的艺术边界的人为性彰显出来。既然小便斗都可以成为艺术品,那还有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既然没有什么不是艺术品,那么艺术边界也就不攻自破了。杜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现代艺术“巫师”,他的《泉》是一个艺术边界的“魔咒”。几百年来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建构确立的艺术边界,在一个现成物致命一击中灰飞烟灭了。美学家费舍尔认为,杜尚的极端现成物解构了视觉艺术最基本的五个假设:1)艺术是手工做的;2)艺术是独一无二的;3)艺术看起来应是完美的或美的;4)艺术应该表达了某种思想;5)艺术应有某种技巧或技艺。 一言以蔽之,杜尚以一种最意想不到却又最有震撼力的方式戳穿了艺术边界的神话。现在,美的艺术这个沾沾自喜于“新衣”的皇帝,一下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众人目前。《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那个所谓艺术的边界,一如黄帝的“新衣”那样并不存在!
说到这里,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悖论性的结论:现代主义在加速划定艺术边界的同时,又无情地摧毁了这个边界。现代主义也许就是艺术自主性所孕育的必定抛弃自己的不肖子孙。
资本逻辑对艺术边界的进一步消解
假如说现代艺术的创新实验和自我张扬在不断地突破原有的艺术边界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社会体制性力量的加入,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艺术的版图。“为艺术而艺术”日益成为一个幌子,一个骗人的把戏。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资本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宰制,艺术也不能幸免于难。得到自主性的艺术并不是存在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里,艺术家要吃饭,他必须养活自己,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作品,他不得不去引起公众和艺术界对其创作的关注。于是,艺术与商业结盟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资本从来就是一个万恶之源,一旦受制于资本的宰制,告别“为艺术而艺术”的终局就为期不远了。今天,我们一次又一次瞥见艺术家“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过是个神话,数不清的艺术家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会变得一反常态,卑躬屈膝,甚至斯文扫地。当代中国艺术的现状即如是。在一个金钱是“硬道理”是社会中,艺术不得不严重地依赖于各种社会的、市场的体制来存活。
从巴托和鲍姆加通到康德,再经过韦伯到哈贝马斯,前面我们勾画了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它揭橥了艺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化中逐渐自立家门的过程。艺术家从过去看主子脸色行事的工匠,变成了独立创作的自由人。在古代社会,今天被我们敬仰的伟大艺术家们其实也不那么伟大,因为他们不过是些被贵族雇佣的家族艺匠而已,仰人鼻息常常是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意而依从主子的喜好。文艺复兴“三杰”,当初也不过是依主子意旨行事的匠人,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为那些显赫家族光宗耀祖而已。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表明,艺术家的人格独立和创作自由是在摆脱了赞助人豢养方式,进入艺术的自由市场之后才获得的。齐美尔说得好,现代货币经济解放了个体,把人从一种传统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因此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是自食其力的自由人,只有在这时个体才获有自我的人格独立,因为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也就不再依赖任何人了。 现代公共领域的发展和艺术品市场化,把艺术家从依附主子的艺匠,转型成自由的创作者。难怪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把自己和神相提并论,将自己誉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这里既有启蒙运动以降艺术家的宏大理想与抱负,又有难以掩蔽的清高、自大和狂妄。遗憾的是,艺术家的这种理想角色从未真正实现过,他们告别了封建家族的赞助人之后,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梵高的一生是一个典型个案,他的大多数作品在生前并不被看好,因此而穷困潦倒一生。他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当你他以几英镑成交的一幅画,会在他死后拍出6千万英镑的天价,这不啻是对艺术家艺术追求的莫大嘲讽!
谁也不曾想到,艺术在好不容易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看护,却又落入了资本宰制的窠臼,好似清晰起来的艺术边界重又模糊起来。平心而论,商业化对艺术来说的确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在斩断束缚和压抑艺术家的种种社会的、道德的和宗教的锁链的同时,又在不经意间揭开了艺术家不食人间烟火而鄙视铜臭的假面。上世纪30年代先锋派艺术不可一世之时,格林伯格就揭露了先锋派艺术家的暧昧。他们一方面自我批判式地为追求为艺术而艺术,另一方面又有一条黄金“脐带”与充满资本铜臭的市场暗中相连。 如今,经纪人、策展人、资助人、收藏夹、拍卖行、博物馆、批评家等体制和角色,如此之多的“看不见的手”扼住了艺术家的咽喉,“工夫在诗外”已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艺术家跟着市场和买家来转悠时,艺术的边界再一次被打得粉碎。艺术品已经沦为和普通商品别无二致的物品。艺术的尊严和斯文也不再被人称道。19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对艺术日益严重的渗透和支配,艺术品市场对艺术风向的左右,拍卖、收藏、投资等商业性活动对艺术品的虚高价格的飙升,在神速造就屈指可数的几个顶尖的艺术富翁的同时,又大多数艺术家抛入一生默默无闻衣食窘迫的困境。如今,艺术并不像哲学家、思想家和美学家所标榜得那样崇高和神圣,也不像艺术家自吹自擂的那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当资本的深度浸湮时,当艺术品流通日趋商业化时,艺术品与其说是一个给人审美愉悦的对象,不如说是蕴含了无限商机和暴利“超级商品”,一个马克思所说的储存交换价值的手段。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与其商品价格已经严重脱节,价格的天文数字与其艺术价值高下已毫无关系。艺术品作为一个异化了的商品,成为金钱发酵的温床。曾被奉为圭臬的纯粹的审美和艺术价值,已经彻底地消解在价格攀升的曲线之中。艺术的边界只依稀留存在人们美好的幻觉里,艺术市场严酷的金钱法则凌越于一切古老的艺术法则之上。鲍德里亚在1987年惠特尼美术馆的演讲中,一方面指出了艺术高度商品化必然消失的宿命,另一方面又坚决否定了回归艺术现代性源头的复辟之路。他说道:
如果商品形式破坏了这对象(指艺术品—引者按)先前的理想性(美、本真性、甚至功能性),那么,无须通过否定商品的本质来尝试使其得以恢复。相反,必须——并且这构成了现代世界反常的和冒险的诱惑之物——使这一断裂绝对化。两者之间不存在辩证关系,综合通常是一种乏力的解决方案,而辩证法通常是一种怀旧的解决。唯一激进的和现代的解决方案:使商品中新奇的、不可预期的、卓越的东西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对有用性和价值保持形式上的冷淡成为可能,使毫无保留地赋予流通以首要性成为可能。这就是艺术品应成为的东西:它应具有在商品里可见的如下特征:令人震撼、新奇、令人惊异、焦虑、流动性,甚至自我毁灭,瞬时性和非现实。
显然,鲍德里亚的方案是激进的和偏颇的,有点像尼采提出的当这个世界衰落不是拯救它,而是给它以致命一击。 艺术中商品的特征越是明显,就将越是迅速地导致艺术的消失,而艺术的边界也就越发难以存在。
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的法则在艺术内部内爆了艺术边界,将艺术推入了危险的困境,艺术越来越像一个充满诱惑的“超级商品”。
后现代与边界的不可能
现代主义在经历百年挣扎后寿终正寝,后现代主义取而代之。从现代到后现代,一系列的反叛、转向和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后现代性不同于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现代的分化实施去分化。去分化意味着曾经被设想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独立艺术领域的消失,把它融入了更为广阔的非艺术空间之中。也许韦伯无法预料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他关于现代性的价值领域分化的判断已被这些领域的去分化所取代。后现代的一系列命题、概念和主义似乎都在模糊艺术的边界,王尔德说的生活模仿艺术到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不再满足于画室创作,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偶发艺术、人体艺术、观念艺术等大行其道。美术馆的艺术空间也被一些艺术家所越界,如有人把国旗从美术馆的封闭空间一直延伸到大街的开放空间,艺术的边界再一次被有意凌越。“日常生活审美化”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精英主义观念,艺术的审美体验不再限于音乐厅、美术馆、剧院或其他体制化的艺术空间,日常起居,衣食住行,甚至锅碗瓢盆的使用都变成了审美体验,因为设计已成为关乎情感体验的一门艺术。 今天,艺术所遭遇的这种状况很像马格利特的《人类状况》那幅画所做的寓言,窗外的风景好比是非艺术的广大生活世界,而画中那个半虚半实的画框恰似艺术,它若隐若现在广袤的实景中,象征着当下艺术所处的不确定形态。不确定性,恰恰就是后现代的基本信念。
美国艺术批评家罗森伯格在1972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艺术的去定义》(The De-Definition of Art)。“去定义”意味着什么?不可定义?无定义?还是反定义?我以为这些意思都是其中应有之义。文中引用了雕塑家莫里斯的一段话真的耐人寻味,莫里斯说:“静态的、可携带的室内艺术物只是一个变得日益无趣的装饰物而已。”请注意,莫里斯这里没有使用艺术品(art work)概念,而是使用了“艺术物”(art object)。从“品”到“物”的用词细微变化,道出了后现代艺术的真谛。“品”是人有意创作出来的东西,而“物”则是无处不在的东西。所以艺术家用“现成物”(ready-made)来取代艺术品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斯这里已经宣判,传统的艺术品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已沦为某种无足轻重的装饰物。1971年,重要的人文杂志《视界》(Horizon)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也可与罗森伯格的书名相呼应,曰《“非艺术”、“反艺术”、“非艺术的艺术”、“反艺术的艺术”都是无用的,如果某人说他的作品是艺术,那就是艺术》(Non-art, anti-art, non-art art, and anti-art art are useless. If someone says his work is art, it’s art.)此话实际上出自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加德,这句话无疑代表了当下艺术家对艺术边界消解的一种普遍判断。
当艺术家忙着颠覆艺术边界时,批评家、理论家和美学家们也没闲着。在一个艺术变得日益恼人的时代,应该说美学家们会有更重要的角色去扮演。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转变过程来看,这角色经历了一个天壤之别的转型。根据社会学家鲍曼的看法,文艺复兴以来,美学家们曾经风光一时。他们曾作为艺术界的“立法者”出现,发动了一个“发现文化“的运动,前面所说的现代性分化导致美的艺术的出现,就是这一运动的产物。他们所以有“立法权”,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论证了艺术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确立了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厘清美的价值标准和批评的原则,建构良好趣味的准则等。他写道:
在整个现代时期(包括现代主义时期),美学家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和艺术判断领域。……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在美学领域,知识分子权力看来尤其未曾受到质疑,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垄断了控制整个领域的权力。……教养良好、经验丰富、气质高贵、趣味优雅的精英人物,拥有提供有约束力的审美判断、区分价值也非价值或非艺术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往往在当他们的评判或实践的权威遭到挑战而引发论战的时候体现出来。
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学家的“立法者”作用,康德、黑格尔、狄德罗、莱辛、歌德、席勒、休谟等一大批美学家可谓典范。曾几何时,随着中产阶级的急剧扩张,大众文化的全面渗透,资本致命渗透导致的商品化,多元文化论的流行,加之后现代艺术的广泛去分化,美学家的“立法者”资格很快就被取消,他们不得不从掌控艺术标准的权威人士,沦落为解释艺术现象的阐释者。比较一下康德与丹托的美学,不难发现两人的巨大差异,后者再也没有前者“要有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那样的勃勃雄心了,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躲在书斋里不那么自信地向一小拨人解释为什么沃霍尔《布里洛盒子》也算是艺术品。
从后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性的来看,艺术无边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为什么要给艺术划出一个确定边界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