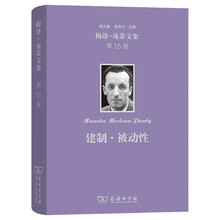因此,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积极意义就在于:真正确定了主体在哲学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说明了客体只能在主体的作用下才能成为客体。认识的对象只能是现象而不能是物自体。这样,康德就将世界划分了两个: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相应地,哲学也分成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是关于现象或认识论的哲学,实践哲学是关于本体或形而上学的哲学。认识和实践这对古老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上被康德明确地划分成为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领域。因此,这场革命的意义可以用康德自己的话来概括:“因此我就得限制知识,以便替信念留余地。”①
在康德看来,最基本的信念就是“人是什么”。因此,形而上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人是最终目的这一目的的问题指示着所有其他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一切哲学都是围绕着人这个目的展开的。在人之外不可能还有哲学的最终目的。即便在人类理性运用的最终目的上,这一问题也为理性运用确定了方向。理性运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这一实用人类学的提问只能作为实践哲学的附属才能够胜任之。因为实用人类学是经验性科学,经验性科学没有普遍性。而实践哲学才是纯粹规范性理论。只有将实用人类学奠基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上,“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才能够获得本质性的解答。所以,他认为,将人的现实性置于哲学中心点的曾经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既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也不能成为哲学的基础,它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终确定了所有哲学方向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哲学基础性问题的无意义性。正是在康德这里,“人的现实性是什么”问题抽身退出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它所据的哲学的中心位置。因此,康德哲学并不是“人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并不是张三、李四等人“类本质”的问题,而是普遍的人性问题,是人的意义问题,是主体的主体性问题。
因此,一方面,康德继续沿着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深入,开始了他对理性的批判性考察,确定了理性的来源,范围和限度,区分了理性的思辨性和实践性,终结了传统认识论,开创了先验哲学,将未来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奠定于实践理性之上;另一方面,在康德称为“本体界”的实践理性这块领域里,呈现的都是先验主体通过意志实行的普遍行为,也可以说是人的形而上学行为。而这样的普遍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这里的人已经不是现实经验的人而是纯粹的自我主体。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不受外界的任何限制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决定自己,即自律性,这便是康德意义上自由的基本蕴义。这种自由一开始就具有存在意义。因为所有道德法则之所以可能便是因为先验主体自由的存在。因此,在实践理性领域中,在人的道德行为里,自由便成为康德道德哲学的“拱心石”。其实,自由也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包括法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哲学的“拱心石”。①
康德搬出自由这块“拱心石”后立即就重新照亮了西方的形而上学。因为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形而上学”几乎就是哲学的代名词。哲学所关心的就是那些普遍的、必然的、无形的、抽象的问题。这样,形而上学也就是成为思辨的代名词。但是,这又同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本性是相悖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哲学或形而上学都是关于人的命运和社会合理秩序普遍原理的学科。在康德看来,这样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理性进行批判所造成的。形而上学成为“抽掉一切经验,而从纯粹概念完全先验地论证一个最高原因的存在”的学科。②这种思辨形而上学同其本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裂。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意义都被彻底地抽空。思辨的本体(Noumena/Noumena)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彻底丧失了存在意义。到康德时代,这种被胡塞尔称为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引起了哲学上一系列混乱和毫无意义的争议,哲学的威望彻底低落。因此,拯救形而上学便成为康德那个时代的使命。所以,通过自由,康德找到了解决一种崭新未来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路径。这便是他实践理性的建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