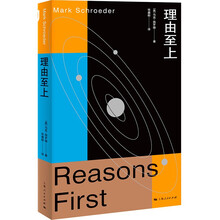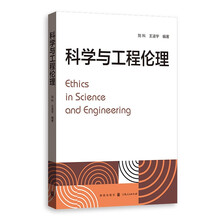前言
儒家实意伦理的中心在于论证儒家伦理的根本在如何于当下一念之间作出“儒家”式道德判断并进而依此行为。本书将从古典儒家伦理论说入手,讨论意念在何种意义上是“儒家的”并且是“伦理的”。“实意”发端于《大学》之“诚意”,在本书里为“实化意念”而实有其意,据此展开一个儒家实意伦理思想系统。全书围绕儒家伦理的十大相关问题展开论述,意图在中西比较哲学的框架下,围绕“实意”与“人缘创生力”的中心议题,考察儒家伦理学涉及的多方面问题。
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在古今中西交汇大潮之下艰难发展,相比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理论推进和学术建构,新生中国哲学学科与时代脉搏交融过分紧密,而在哲学理论的突破上则乏善可陈。在今天这样一个东西方学术充分交流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借助西方哲学的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先哲的哲学理论进一步学术化、系统化,凸显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蕴意。本书希望将儒家经典中的伦理思想,通过与西方哲学尤其是美国实效主义(pragmatism)pragmatism通常译成“实用主义”,但由于该词语在汉语语境中有着通俗的贬义,以致在哲学理解方面已经造成不少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本书中将主要译成“实效主义”,借以强调美国哲学实用主义注重效果的哲学内涵,而其功利主义的一面并没有一般理解的那么重要。哲学的对话,建构一个儒家实意伦理学理论系统。
在现代哲学学术研究的大背景下,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表述显得较系统性。今天要建构儒家伦理理论,既要借鉴近代以来系统性整理的古代哲学家的伦理思想资料,还当借鉴西方将中国哲学思想系统化的学术成果。西方关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系统化的哲学传统,往往有试图将中国古代思想系统化的倾向。比如陈汉生《中国思想的道家理论》试图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建构系统性的论述。CfChad Hansen,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 在中西方讨论儒家伦理的哲学叙述中,系统化建构儒家伦理学的哲学理论多运用西方伦理学体系,如德性伦理、规范伦理等理论来诠释儒家伦理思想。本书希望另辟蹊径,以期在把握传统儒家伦理精神核心的前提下,回应相关伦理问题的不同维度。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近代国际伦理学界大有复兴之势,而关于亚氏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比较研究也多有成果。不过,中外学者在理论比较之余,很少注意到亚氏认为人的美德主要由社会环境教化而成,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至于人成人之后当如何自修,继续保持和培养美德,他的讨论远远没有儒家的“修身”有力。同样,休谟伦理学思想作为当代伦理学复兴的重要理论源头,也缺乏关于人如何自修保持美德的理论建构。西方伦理学讨论自我、自由意志、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等等,表面上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但如何与情境互动,做合理的决定以期达到自我的成就,西方伦理学却缺乏完善的理论。西方社会把如何做人生决定的艺术主要交给宗教,而教会的教导通常只给出一条出路,那就是制止内心的原罪,趋向唯一的、上帝认可的标准,或者《圣经》明示的、经过解释的标准。相比之下,中国伦理学则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出路,心灵遵从儒、释、道之教化而做决定,皆有可能成为圣人、善人,这样,成善的修身过程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更没有非此即彼的善恶之战。这就是实意、实化意念,而不是意念善恶之战的由来。与强调天然内在、自然从善的美德伦理学不同,儒家伦理学强调个人不是自然向善,而是主动择善而从,也就可能在意念发动的瞬间赋予其善的价值。儒家的德性不是天生的美德,而是后天实意形成的德性的累积,通过努力修为而得。外在的教化并不保证人能够向善和择善,只有内心的意念发动向善,并让意念持续实化为善性,德行方能建立,德性方能彰显。
关于儒家伦理学的研究固然已经汗牛充栋,但多数是描述其特征的讨论,而从人自身本有的创生力出发,阐释儒家伦理学何以可能的学理建构相当有限。葛瑞汉指出,墨家的伦理学比较系统化,质朴完整且有一致性,相比之下,儒家几乎从未也未曾试图去建立一个类似的有序系统。CfAC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03, p45.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在今天带有比较哲学的意味,而儒家伦理学的哲学系统化当在近代以来东西哲学对话日益深化之后才成为可能。杜维明在《人性与自我修养》一书中,以《“仁”与“礼”之间的创造紧张性》开篇,并说明这是他问题意识的最初发端。参见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联经中文版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2。
虽然这里建构的是儒家传统伦理学命题的当代哲学化版本,但儒家实意伦理学的现代使命仍然在于导人向善,其出发点与孟子和亚里士多德追求人性之善与后天如何为善并二致。儒家实意伦理学作为当代哲学理论仍然应当具备改变人心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反思人伦关系,并在人伦关系实践中持续其创造的力量。从原始儒家开始,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人应当受到教化并被导之向善,虽然后来兴起的道家和佛教也导人向善,但在教化的一念之间,儒道佛的分野立现。虽然表面上殊途同归,都是改变人心意向的方式,但儒家之谓儒家,定然有其不可移易的力量在。
儒家伦理学其实从一开始就一直面对一个难题,即改变自己和他人心向的努力何以是“儒家的”?一个人改变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前提是改变自己的内心,进而创造性地改变自己内心原先设定的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但人的内心何以能够具备创造新的与他人关系的力量?这种内心之中创造的力量又如何随着外在的情势而改变?儒家实意伦理学力图论证:论是内心的改变抑或情势的改换,人与他人关系的改变都离不开对既有存在之境的理解和基于人缘创生力的涵养。虽然心向的改变有其肉体自然存在作为基础,但心灵对情势的领悟和通过实意改变其情境则首先基于心灵对自身与世界共在的理解。正是在心灵与世界共生之境的本体论基础上,本书力图论证实意的努力何以可能是伦理的。
在本书中,将儒家伦理哲学化的主要哲学参照是实效主义哲学关于人生与世界的观点。实效主义哲学的真理有当下性和效用性,比如,对于航海迷路的航船,船上牧师和水手的争辩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以何者最终有效作为判断的依据。如果牧师说服水手放弃航行的技术,通过信仰上帝获得心灵的平静以面对死亡,上帝的信仰就是有效的;如果水手用技术带领牧师走出了迷途,则科学就战胜宗教而成为有效的。这个例子说明实效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各种不同传统之间都存在真理选择时的方向感的区别。以这种真理观为代表的美国实效主义传统认为只要有实际效果,就当持乐观的生活态度。相形之下,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儒释道三种传统都注重治心的实际效果,都可以归结到选择的哲学,如何将人从意识的人生中梳理出一种可以由意识主导的选择模式,化被动为主动。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美国实效主义哲学传统不如中国哲学传统强调选择的方向感。有用与有效指向当下,并不指向未来。而中国哲学传统多指向未来,强调理想的人格,认为当下的工夫都要以成就未来的理想人格作为指归。儒释道都有一定的价值理念作为导向,超越“趋利避害”的基本生存要求和自然倾向。人的选择有其情境固然没错,但为何如此选择则不仅仅是在情境中用实效主义的原则即可得到完满的答案。即使在詹姆士走出丛林的例子中,其强调的选择方向也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即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的要求。而生存疑只是生活的最低标准,生命的伦理展开所需要实现的应当是远远高于生存层面的目标。这是中国哲学与美国实效主义之间价值导向的区分。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建立儒家实意伦理学的价值导向系统的。
从儒家的角度看,人类心灵方向的改变,进而改变与他人的关系是如何可能的?人如何才能通过对心灵本体的领悟进而改变心灵的方向?我们应该如何领悟心灵本体?我们改变心灵的方向,除了趋善避恶的本能之外,对心灵的控制是否可以有纯粹的伦理和审美意味?举例来说,心灵对于既有规则的认知,好比驾驶员意识到交通规则的存在和道路的实存,但对车的驾驶,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每时每刻对车的驾驭,都是以对车的存在以及车与道路和交规等共在的场域之间的领悟作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把心灵如何指导行动改变,化为驾驶者如何在领悟自身与情境共在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心跟车及道路之间构成的场域的微妙关系,那么驾驶的技能就可以理解为作为行为主体的驾驶员如何提升自己的驾驶技巧,好比伦理关系中的人如何获得和涵养内在的德性,而内在德性经过修养又转化为行为的自然倾向。开车和游泳这类技艺都可以算是通过实践不断内化形成内在德性的艺术,相应地,在实践中的道德过程也是一种需要涵养而逐渐内化的艺术,并在每时每刻的人伦关系中表现出来。当然,即使良好的德性也不能保证永不犯错,正如优异的车技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良好的游泳技能不能保证游泳者在汪洋大海中安然恙一样。可见,个体对人伦关系创造过程就像开车和游泳的过程一样,是不断将心灵的方向实化出来,并通过外在实践而内化的行为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力图使得个体与人伦关系构成的情势处于和谐之境。
开始于孔孟的儒家伦理一方面强调内心善的先验性,需要人不断回到先天善性开始的地方去体验并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也强调人心所发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应当努力修身以合于礼制规范的要求。人伦关系的和谐之境是儒家伦理的永恒目标。可见,儒家伦理是一种合乎情境的实意伦理。人因肉身的实存而有意识,而对意识的修炼构成人在世界之中创造自己人生轨迹的必经之路,而儒家对意念真诚至极的提倡,构成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底色。人因为能够将其意念实化而与外在情境沟通,既受情境的影响,也创造情境,这就是人与外在人与物之间的“缘”的开端,而对于“缘”的领会和把握,构成了人在世间的伦理创造力的根源。这种人与其情境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儒家对于人在世间存在的领悟的审慎状态,由此出发行使道德权利和实践道德行为,并推己及人。儒家能够从自身推致他人的基石源于孝悌的良心和良知,并在这种先天善性的基础上实化意念以实践道德选择,这就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情理。这种情理发用于社会交往与实践,就是对自身天然权利的理解和领悟,进而扩展自己的权利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家与国之间,儒家的先天道德能力与实践原则却与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儒家最终还是回到对人的先天存在及其先验善性的家庭情感来源的基石上,给出对于家国矛盾的解答。儒家在家国关系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民主观念的接受,以及在中国政治理论话语的当代转化中,如何协调与解决主与民的关系。
儒家实意伦理学是人在经验与世界全体融贯的境界里建立道德价值的伦理学。人生态度则要努力运世之化,既有哲学建构,又有道德运用,还有美感价值。这些都是在创生力展现为“实意”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面对纷杂的世态人情,哲人们希望把它们解释得合情合理,就必须找出使人情世故变得有序的根源所在。儒家经典确定了人己关系的原初性韵味,也就是人如何在一个“生生”不息的万物情境中把握自我、发展自我、修养自我。用杜威的话说,自我与他人相关联要穿透自身,与他者连通并共同创生。儒家之家庭观与杜威的社群观都关心群己关系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表现形式。可以这样说,自我观念在儒家家庭与杜威社群同缘异构的交融中,不断展示出其在全球化情境中的新生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哲学的悠久文化传统,充分注意到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尤其是当代中国一直被动回应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对自身话语系统的自信。我们需要回归古典儒家哲学,调动近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对话的资源,结合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情形来综合考察,从实意创生的角度,将传统儒家伦理学在实意哲学的框架内建构成为儒家实意伦理学。
实意伦理学,也就是让当下的意念坚实,从而实现“念下转命”的伦理思想,这跟传统实践儒家伦理生活的目标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在意念的反思状态中去粗存精,将合适的意念坚实,从而使心境广大,念及世界苍生万物,进而成就意念对世界的实际作用,以及人生的意义。论是儒家伦理涉及的哪一个层面,都可以回归到儒家对于人之实存的理解,以及基于实存的人之心意所发的实化过程,这就是儒家伦理中人伦创生力的维度。本书通过阐发传统儒家从实意到人缘创生的各种维度建构一个传统儒家伦理的新哲学版本。
哲学家们使用的范畴有公共的意义,但同时也有哲人本身赋予的特殊意义,而且这些被赋意的新范畴往往会成为未来哲学思想的源生力量。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伦理维度相当明显,历史上先秦伦理学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哲学化的过程,也就是伦理哲学范畴的内涵不断深化的过程。本书将赋予传统儒家伦理范畴以新的哲学意义,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善与缘、身与意、境与生、己与人、意与义、孝与仁、情与礼、人与权、家与国、主与民各范畴的新意与其间的中道。这是儒家伦理学在当代中西哲学对话中的必然处境,落实到儒家伦理学与当代哲学,尤其与美国实效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存在状态的哲学对话之中,建构起一个儒家伦理学的当代哲学化版本。儒家实意伦理学说明,人可以通过更好地理解人与他人的共生关系来创造有价值的生活情境,这一哲学观有助于振兴儒家伦理传统,并为中西哲学对话的深入指明新的方向。
今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不是完全现代化,只是从国际视角来看,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工业化。三十年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比较快地嫁接了现代化的很多理念,从而可能直接进入后现代的状态。所以儒家伦理学的现代转化要自觉地放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而不要纠缠在现代性的话语中不放。儒家伦理学的后现代转化主要是加强学理研究,回应西方一整套学理的冲击,努力把传统儒家伦理学转化成为能够回应西方成型的学理系统的新理论体系。儒家伦理学应当从其核心范畴入手承担起回应西方哲学冲击的历史责任。
在三十年中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如今政治伦理话语似乎处于失语状态,在政治伦理话语的各种版本之间犹豫不定,与一个巨大的未曾间断的数千年文明所应当具有的政治伦理话语传统极不相称。“实效主义”(pragmatism)哲学思想在中国往往被简约为“黑猫白猫”和“摸石头”的朴素实效主义版本,不能够与传统儒家伦理发生良好的沟通互动。过分朴素的实效主义版本既跟西化之后的政治伦理学智慧关联不大,又跟传统的千年文明缺少交集。可见,一个新版本的政治伦理话语系统既得吸收西方政治伦理学的精神,又得立足于古典政治伦理学经典的智慧。应该说,一个新版本政治伦理话语的原点应该跳出西方政治话语的俗套,寻求一种新的中道。
中道作为传统儒家伦理学的根本精神,如今已经黯然失色,因为将其付诸实践难乎其难。现实实践的中道微妙难求,理论形式的中道更是难以捉摸。“中庸不可能也”早就是经典文本的感叹,但这又疑是成熟政治伦理生态的呼唤,希望传统儒家伦理得到重新阐发和发挥。本书虽是一部关于“儒家实意伦理学”的著作,但还是希望能够在章节的字里行间,恢复传统儒家伦理的中道气象。作者相信,在善与缘、身与意、境与生、己与人、意与义、孝与仁、情与礼、人与权、家与国、主与民之间寻求中道,既是传统政治伦理话语的微妙境界,也是今天中西比较哲学语境下中国政治伦理话语转换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国思想者和哲学家需要走出现代性议题及其话语体系,不再围绕西方现代性和普遍主义的种种议题打转。如果几乎所有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讨论,都离不开“民族国家”等现代性极强的术语,而发问的开端几乎都是“为什么中国不是”,那么中国自本自为的话语体系将从恢复和建构。尤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史前例的新型国家面前,中国思想者和哲学家需要体会和提升中道的精神,在理论建构中体现出折中百代的气魄,以葆养和发扬原初文化气脉延续至今的动态平衡之精神,化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冲击于形。这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而儒家哲学及其伦理思想,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儒家实意伦理学植根于百年来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背景,力求对中西伦理对话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以独立的思考与解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