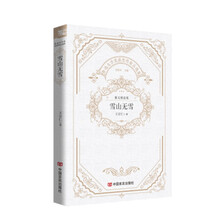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中西学术思想之异,如宗教思想发达与否,哲学路向同否,科学思想发展与否,即此三大端,中西显然不同。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不独儒者如此,道家更务克治其情,以归恬淡。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之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见而放弃神的观念,既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于人间之企图。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中国人非无宗教思想,庶民有五祀与祖先,即多神教。上层人物,亦有天帝之观念,即一神教。但因其知力不甚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渐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有客观的大神;即在下层社会,祭五祀与祖先,亦渐变为行其心之所安的报恩主义,而不必真有多神存在,故祭如在之说,实中国上下一致之心理也。中国人唯反求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与宇宙元来不二。
孔子赞《易》,明乾元统天,乾元,仁也。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万物同具之生生不息的本体。无量诸天,皆此仁体之显现,故曰统天。夫天且为其所统,而况物之细者乎。是乃体物而不遗也。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参考《新唯识论》语体本《明心章》。庄生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灼然物我同体之实。此所以不成宗教,而哲学上,会物归己,用僧肇语,陆子静言宇宙不外吾心,亦深透。于己自识,即大本立。此中己字,非小己之谓。识得真己,即是大本。岂待外求宇宙之原哉。此已超越知识境界,而臻实证。远离一切戏论,是梵方与远西言宗教及哲学者所不容忽视也。《新唯识论》须参考。中国哲学归极证会,证会则知不外驰。外驰即妄计有客观独存的物事,何能自证。情无僻执。僻执即起倒见,支离滋甚,无由反己。要须涵养积渐而至。此与西人用力不必同,而所成就亦各异。
科学思想,中国人非贫乏也。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指南针自周公。必科学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此重大发明。未可视为偶然也。工程学在六国时,已有秦之李冰,其神巧所臻,今人犹莫能阶也。非斯学讲之有素,岂可一蹴而就乎。张衡候地震仪,在东汉初。可知古代算学已精,汉人犹未失坠。余以为周世诸子百家之书,必多富于科学思想,秦以后渐失其传。即以儒家六籍论,所存几何。孔门三千七十,《论语》所记,亦无灵语。况百家之言,经秦人摧毁,与六国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后大一统之局,人民习守固陋,其亡失殆尽,无足怪者。余不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思想。但以之与希腊比较,则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或仅为少数天才之事,而非一般人所共尚。此虽出于臆测,而由儒道诸籍,尚有仅存,百家之言,绝无授受,两相对照,则知古代科学知识非普遍流行,故其亡绝,易于儒道诸子。此可谓近乎事实之猜度,不必果为无稽之谈也。中国古代一般人嗜好科学知识不必如希腊人之烈。古代由儒家反己之学,自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以来,素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及道家思想与儒术并行之情形以观,正可见中国人知不外驰,情无僻执,乃是中国文化从晚周发源便与希腊异趣之故。希腊人爱好知识,向外追求,其勇往无前的气概,与活泼泼的生趣,固为科学思想所由发展之根本条件,而其情感上之坚执不舍,复是其用力追求之所以欲罢不能者。此知与情之两种特点,如何养成,吾以为环境之关系最大。希腊人海洋生活,其智力以习于活动而自易活跃。其情感则饱历波涛汹涌而无所震慑,故养成坚执不移之操。中国乃大陆之国,神州浩博,绿野青天,浑沦无间,生息其间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神妙万物,无知而无不知。妙万物者,谓其智周万物而实不滞于物也。不琐碎以逐物求知,故曰无知。洞彻万物之原,故曰无不知。彼且超越知识境界,而何事匆遽外求,侈小知以自丧其浑全哉。儒者不反知,而毕竟超知;道家直反知,亦有以也。夫与天地同流者,情冥至真而无情,即荡然亡执矣。执者,情存乎封畛也。会真则知亡,有知,则知与真为二。非会真也。而情亦丧。妄情不起曰丧。故无执也,知亡情丧,超知之境,至人之诣也。儒道上哲,均极乎此。其次,虽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也。
就文学言,希腊人多悲剧。悲剧者,出于情之坚执,坚执则不能已于悲也。中国文学以《三百篇》与《骚经》为宗。《三百篇》首《二南》,《二南》皆于人生日用中,见和乐之趣,无所执,无所悲也。《骚》经怀亡国昏主托于美人芳草,是已移其哀愤之情,聊作消遣。昔人美《离骚》不怨君。其实,亡国之怨,如执而不舍,乃人间之悲剧,即天地之劲气也。后世小说写悲境必以喜剧结,亦由情无所执耳。使其有坚执之情,则于缺憾处,必永为不可弥缝之长恨,将引起人对于命运或神道与自然及社会各方面提出问题,而有奋斗与改造之愿望。若于缺憾而虚构团圆,正见其情感易消逝而无所固执。在己无力量,于人无感发。后之小说家承屈子之流而益下,未足尚也。要之中国人鲜坚执之情,此可于多方面征述,兹不暇详。
就哲学上超知之诣言,非知不外驰,情无僻执,无由臻此甚深微妙境界。然在一般人,并不能达于哲学上最高之境,而不肯努力向外追求,以扩其知。又无坚执之情,则其社会未有不趋于委靡,而其文化,终不无病菌之存在。中国人诚宜融摄西洋以自广,但吾先哲长处,毕竟不可舍失。
或问曰:西方文化无病菌乎?答曰:西洋人如终不由中哲反己一路,即终不得实证天地万物一体之真,终不识自性,外驰而不反,只向外求知,而不务反求诸己。知识愈多,而于人生本性日益茫然。长沦于有取,以丧其真。有取一词,借用佛典。取者,追求义略言之,如知识方面之追求,则以理为外在,而努力向外穷索,如猎者之疲于奔逐。而其神明恒无超脱之一境,卒不得默识本原,是有取之害也。欲望方面之追求,则凡名利权力种种皆其所贪得无厌而盲目以追逐之者,甚至为一己之野心与偏见,及为一国家一民族之私利而追求不已,构成滔天大祸,卒以毁人者自毁。此又有取之巨害也。是焉得无病菌乎!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并心外驰,知见纷杂,而不见本原,无有归宿,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
(答张东荪)弟以病躯,常有神伤不敢窥时报之感;故未阅《晨报》。昨闻人言,兄有一文,题曰《中西哲学合作的问题》,登在《北平晨报》《思辨》栏,系对弟前登天津《大公报》一文而发者。弟固素喜闻吾兄之言论,因觅取一读。关于合作一词,弟前文中尚未用及,只有如下数语。愚意欲新哲学产生,必须治本国哲学与治西洋哲学者共同努力。彼此热诚谦虚,各尽所长。互相观摩,毋相攻伐。互相尊重。毋相轻鄙。务期各尽所长,然后有新哲学产生之望,云云。
兄或即由此段文字,而判为主张合作,实则与尊意所谓中西分治,元是一致也。分治之说,自社会言之,却是完成合作,如造针厂然。锻铁乃至穿鼻等等,人各分工而治,恰恰以此完成合作之利。但就个人治哲学而言之,是否应当中西兼治,弟颇因尊论而愿有所言。常以为如有人焉,能尽其诚,以兼治中西之学,而深造自得,以全备于我,则真人生一大快事。更有何种理由,能言此事之不应当耶?如兄引荀子书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此段话,确足代表东方各派哲学底一致的根本精神。中国儒道诸家如是,印度佛家亦如之。佛家经典,形容佛身一一毫端放大光明,表示宇宙底清净就在他身上实现着。易言之,他就是真理显现。所以他说真如一名法身,不是当作所知的外在境界。特各家所造自有浅深,此姑不论。然此等实践的精神,即把真理由实践得到证明。人只要不妄自菲薄,志愿向上,则从事此等学问,用一分力,有一分效,用两分力,有两分效。谁谓治西洋
哲学者对中国哲学,便当舍弃不容兼治耶?尊论云,中国人求学的动机是求善,而不是求真。西方人的求知,志在发掘宇宙的秘密。便和开矿一样,其所得是在外的,与得者自身不必有何关系。所以西方能成功科学。这个态度,是以求知道实在为目标,不是当作一个价值来看。总之,西方人所求的是知识,而东方人所求的是修养。换言之,即西方人把学问当作知识,而东方人把学问当作修养。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异点。此段话,是真见到中西文化和哲学根本不同处。非精思远识如吾兄者,何能道及此?但吾兄必谓中西可以分治,而不堪融合,则愚见适得其反。吾侪若于中国学问痛下一番工夫,方见得修养元不必摒除知识,知识亦并不离开修养。此处颇有千言万语,当别为详说。唯于兄所谓西学求真,中学求善之旨,是以真善分说。弟不必同意。兄云,西人态度,以求知道实在为目标。则所谓真者,即实在之异语。然实在之一词,或真之一词,似宜分别其用于何等领域之内,方好判定其涵义。而西洋哲学家真善分说之当否,亦将视真字之意义为何,然后可论。弟意哲学实只玄学所求之真或实在,与科学所求之真或实在,本不为同物。科学所求者,即日常经验的宇宙或现象界之真。易言之,即一切事物相互间之法则。如凡物皆下坠,凡人皆有生必有死,地球绕日而转,此等法则,即事物之真,即现象界的实在。科学所求之真即此。但此所谓真,只对吾人分辨事物底认识的错误而言。发见事物间必然的或概然的法则,即得事物底真相。没有以己意造作,变乱事物底真相,即没有错误。故谓之真。是所谓真底意义,本无所谓善不善。此真既不含有善的意义,故可与善分别而说。西洋人自始即走科学的路向,其真善分说,在科学之观点上,固无可议。然在哲学之观点上亦如之,则有如佛家所斥为非了义者。此不可不辨也。哲学所求之真,乃即日常经验的宇宙所以形成的原理,或实相之真。实相犹言实体。此所谓真,是绝对的,是无垢的,是从本已来自性清净。故即真即善。儒者或言诚,诚即真善变彰之词。或但言善,孟子专言性善。而真在其中矣。绝对的真实故,无有不善。绝对的纯善故,无有不真。真善如何分得开?真正见到宇宙人生的实相的哲学家,必不同科学家一般见地,把真和善分作两片说去。吾兄谓中人求善,而不求真,弟甚有所未安。故敢附诤友之末,略为辨析。总之,中国人在哲学,是真能证见实相。所以,他总在人伦日用间致力,即由实践以得到真理的实现。如此,则理性、知能、真理、实相、生命,直是同一物事而异其名。此中理性知能二词,与时俗所用,不必同义。盖指固有底而又经过修养的之明智而言。中人在这方面有特别成功。因此,却偏于留神践履之间,如吾兄所谓本身底修养,便不能发展科学。吾前言,修养,不必摒除知识。须知不必云云,则已不免有忽视知识的趋势。周子曰: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富哉斯言!古今几人深会得?凡事势流极,至于天地悬殊者,其肇端只在稍轻稍重之间,非析理至严者莫之察也。易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昧哉斯言也!罗素常说,喜马拉雅山头一点雨,稍偏西一点,便落入印度洋去,稍偏东一点,便落入太平洋去。中人学问,起初只是因注重修养,把知识看得稍轻,结果便似摒除知识,而没有科学了。西人学问,起初只因注重知识,所以一直去探求外界的事物之理。他也非是绝不知道本身的修养,只因对于外物的实测工夫,特别着重,遂不知不觉的以此种态度与方法,用之于哲学。他遂不能证得实相,而陷于盲人摸象的戏论。因此,他的修养,只是在日常生活间,即人与人相与之际,有其妥当的法则。此正孟子所讥为外铄,告子义外之旨即此。后儒所谓行不著,习不察,亦谓此等。中人的修养是从其自本自根,自明自了,灼然天理流行,即实相显现。而五常百行,一切皆是真实。散殊的即是本原的,日用的即是真常的。如此,则所谓人与人相与之际,有其妥当的法则者。这个法则的本身,元是真真实实,沦洽于事物之间的,可以说事物就是由他形成的。若反把他看作是从人与人底关联中构成的,那法则便是一种空虚的形式。这等义外之论,是不应真理的。所以言修养者,如果不证实相,其修养工夫,终是外铄。所以站在东方哲学的立场,可以说,西人的修养工夫,还够不上说修养,只是用科学的知识,来支配他的生活,以由外铄故。或谓康德一流人,其言道德似亦不是外铄的,可谓同于东方哲人的修养否?此则不敢轻断。然康德在谈道德方面,亦承认神的存在。此为沿袭宗教思想,且与科学计度外界,同其思路。斯与东方哲学复不相类。总之,西人学问,纵不无少数比较接近东方者。然从大体说来,西人毕竟偏于知识的路向,而距东方哲人所谓修养,不啻万里矣。有谓吾兄以修养专属中人为不必当者,是乃粗疏之见也。如上所说,可见中西学问不同,只是一方,在知识上偏著重一点,就成功了科学。一方,在修养上偏著重一点,就成功了哲学。中人得其浑全,故修之于身而万物备,真理元无内外。西人长于分析,故承认有外界,即理在外物。而穷理必用纯客观的方法。中西学问不同,举要言之,亦不过如此。弟数十年来,感于国人新旧之争,常苦心探索其异处。常闻明季哲人方密之遗书,谓中学长于通几,西学长于质测。通几由修养而得,质测乃知识所事。其与吾侪今日之论,犹一辙也。弟唯见到中西之异,因主张观其会通,而不容偏废。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而殚精竭力,以从事于东方哲学之发挥。《新唯识论》,所由作也。是书,今人盖鲜能解者。吾兄一向用功,亦不同此路数,或不必同情此书。弟因触及素怀,便及此事,要不欲外所旁论,窃以为哲学与科学,知识的与非知识的即修养的宜各划范围,分其种类,辨其性质,别其方法。善侪治西洋科学和哲学,尽管用科学的方法,如质测,乃至解析等等。西洋哲学,从大体说来,是与科学同一路子的。虽亦有反知的哲学,较以东方,仍自不类。治中国哲学,必须用修养的方法,如诚敬,乃至思维等等。孔、孟恒言敬、言诚,程子《识仁篇》云以诚敬存之,朱子所谓涵养,即诚敬也。孔、孟并言思,孟云不思即蔽于物,甚精。孔云思不出位者,此犹佛家所谓思现观,不流于虚妄分别,不涉戏论,是谓思现观,是谓思不出位。宋以后儒者,言修养,大抵杂禅定,而思唯之功较疏,宜反诸孔、孟。道并行而不相悖,正谓此也。修养以立本,则闻见之知,壹皆德性之发用,而知识自非修养以外之事。智周万物,即物我通为一体。不于物以为外诱而绝之,亦不于物以为外慕而逐之也。孔、孟之精粹,乃在是耳。孔、孟主修养,而未始反知也。当此中西冲突之际,吾侪固有良好模型,又何必一切唾弃之哉!
尊论有云:若以西方求知识的态度,来治中国学问,必定对于中国学问,觉得其中甚空虚,因而看得不值一钱。此数语,恰足表示今人对于中学的感想。老子绝学无忧之叹,殆逆料今日事矣。忆弟年事未及冠,似已得一部《格致启蒙》,读之狂喜。后更启革命思潮。六经诸子,视之皆士苴也。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詈。及长而涉历较广,综事比物,自审浮妄。转而读吾古书,旷观群学,始自悔从前罪戾,而不知所以赎之也。中国学者,其所述作,不尚逻辑,本无系统。即以晚周言之,《论语》《老子》,皆语录体。《庄子》书,则以文学作品,发表哲学思想。《易》之《十翼》,特为后儒传疏导先路。即法家墨家故籍稍存者,条理稍整,亦不得称为系统的著作。故有志中学者,恒苦古书难读。非徒名物训诂之难而已。其文无统纪,单辞奥义,纷然杂陈,学者只有暗中摸索,如何不难?此其难之在工具方面者也。至于儒道诸家,所发明者,厥在宇宙真理,初非限于某一部分底现象之理。这个道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遣,《系传》形容得好。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中庸》形容得好。故高之极于穷神知化,而无穷无尽,近之即愚夫愚妇与知与能。至哉斯理,何得而称焉。赫日丽天,有目共见,有感共觉。感谓热度之感。无目无感者,不见不觉,遂詈,称阳宗之显赫。今之谓中国学问不值一钱者,何以异是。尤复当知,中国学问,所以不事逻辑者。其从所入,在反己,以深其涵养,而神解自尔豁如,然解悟所至,益复验之实践。故阳明知行合一,实已抉发中国学问之骨髓。其视逻辑为空洞的形式的知识,宜所不屑从事。但此与西洋学问底路子,既绝异而无略同者。今人却自少便习于西学门径,则于本国学问,自不期而与之扞格。此其难之在于学子之熏习方面者也。虽有诸难,然只将中西学问不同处,详与分别,则学者亦可知类而不紊,各由其途而入焉。久之,则异而知其类,睽而知其通,何乐如之!
尊论又云:倘使以中国修养的态度来治西方学问,亦必觉得人生除为权利之争以外,毫无安顿处。此段话,弟亦不无相当赞成。然终嫌太过。兄只为把知识持作与修养绝不相容,所以有这般见解。在西人一意驰求知识,虽成功科学,由中国哲学的眼光观之,固然,还可不满足他,谓之玩物丧志。甚至如兄所云权利之争等等。然若有一个不挟偏见的中国学者,他必定不抹煞西人努力知识的成绩,并不反对知识。只须如阳明所谓识得头脑,即由修养以立大本,则如吾前所云,一切知识,皆德性之发用。正于此见得万物皆备之实,而可玩物丧志之有。西人知识的学问底流弊,诚有如吾兄所谓权利之争。要其本身不是罪恶的,此万不容忽视。如自然对于人生底种种妨害,以及社会上许多不平的问题,如君民间的不平,贫富间的不平,男女间的不平,如此等类,都缘科学发展,乃转逐渐以谋解决。此等权利之争,即正谊所在。正如佛家所谓烦恼即菩提。现代卑劣的中国人,万不可误解此义而谬托于此,千万注意。何可一概屏斥?东方言修养者,唯中国道家反知识,恶奇技淫巧,此在今日,不可为训。儒家元不反知,弟前文已说过。印度佛家,本趣寂灭。然及大乘,始言无住涅槃。生死涅槃两无住著。名无住涅槃。小乘只是不住生死,却住着涅槃。及至大乘,说两无住。即已接近现世主义。又不弃后得智。彼说后得智是缘事之智,即分辨事物的知识。此从经验得来,故名后得。斯与儒家思想,已有渐趋接近之势。然趣寂之旨,究未能舍。此吾之《新论》所由作也。《新论》,只把知识另给予一个地位,并不反知。儒家与印土大乘意思,都是如此。弟于《大学》,取朱子《格物补传》,亦由此之故也。朱子是注重修养的,也是注重知识的。他的主张,恰适用于今日。陆、王便偏重修养一面去了。
弟于此一大问题,研索甚久,自有无限意思。惟以五十病躯,略无佳趣。提笔便说不出来。拉杂写此,不知吾兄于意云何。尊意有所不然,即请尽情惠教。又此信,以东方之学为哲学,自时贤观之,或不必然。但弟素主哲学只有本体论为其本分内事。除此,多属理论科学。如今盛行之解析派,只是一种逻辑的学问,此固为哲学者所必资,然要不是哲学底正宗。时贤鄙弃本体论,弟终以此为穷极万化之原,乃学问之归墟。学不至是,则睽而不通,拘而不化,非智者所安也。见体,则莫切于东方之学。斯不佞所以皈心。此信,请与张申府先生一看。吾与彼主张本自不同,但同于自家主张以外,还承认有他。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