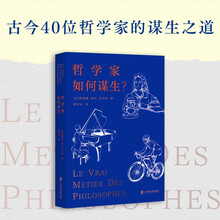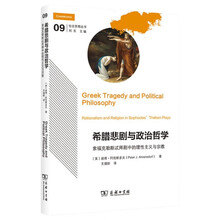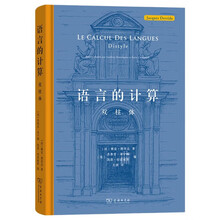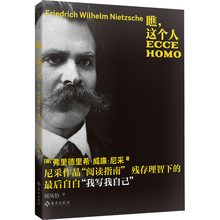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引人深思的是,直到18世纪之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柏拉图的作品似乎一直是学园内部的秘学。随着形而上学在近代成为显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品迅速取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近人对色诺芬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翻开20世纪的各色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不是受到奚落(比如大名鼎鼎的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干脆忽略不计。在西方学界,20世纪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性”柏拉图学术研讨会,却似乎从未召开过以色诺芬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一本书——《回忆苏格拉底》,时在2003年。
在20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我们出国留洋,如果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类专业学科没有自觉的反省意识,那么,回国以后,我们除了会用洋博士身份自娱,恐怕不会对中国的学术建设有什么实际意义。比如,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很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孔子,但按照19世纪的德国学界确立起来的古典学传统,我们会继续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古工坊
2011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