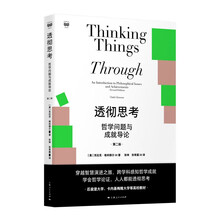4
在对标题“争辩”的字面阐明中(这种“争辩”当在外部刻画出他与尼采的深入的解释性对话),当海德格尔同时把“自行设为统一”(Sich—ineins—setzen),即一种试图在其全部的重要性中把尼采视为不同的思想家的尝试,理解为透镜的焦点(在这个焦点上这位不同的思想家必然显得遥远并且进入最大程度的疏远中),这时候,他已经明确提出了从与尼采的遭遇中产生出来的思想问题。海德格尔对尼采思想所给予的细致关注(这种关注最为明确地与20世纪尼采解释的“德国戏剧”区分开来)因此本质上归属于争辩的总体关联:不能忽视的是,当“我们正下降到其中的最后事实”,即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最具深渊性的思想”之间的共属一体性重又变得明朗,抑或是当海德格尔恰恰在一种总体关联中(存在的原初的存在之真理,与尼采的以身体为主线的生物主义和哲思活动的严格的自身~区分)坚持这样一点,即尼采的生命概念不应与同时代人无思的种族主义式的生物主义相“混同”,这时候,他的阐释过程不光是打断了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化的歪曲和断章取义。所有这些都已经为人们所充分了解,正像海德格尔发掘尼采“形而上学”的内在构造并同时打破被假定为“遗著”的《权力意志》的布局的尝试一样。单个的笔记顺序及其时间定位在海德格尔的解释中已经得到了悄无声息的实行(这规定了日后的、权威的尼采编辑工作)。而解释的任务才因以刚刚起步,因为这些岛屿一般的基本元素间的总体关联还有待追问。尼采的语句应该像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基本规定的陈述一样,得到细致掂量,它们必须得到研究从而作为对其进行解释的准备。海德格尔对尼采文本的阅读与思考操练因此可以始终成为思想在完全的晦暗中谨慎而行的最值得注意的证据之一。此间的这种阅读与思考操练还包含着远远超出其时间和地点的,对任何尼采阐释而言都具有典范意义的特征。因为即便在海德格尔觉察到“尼采的风格”以及玲珑多变的语言和书写面具的地方——海德格尔的阅读和思考操练对于这些东西毫无疑问地并没有投以关注——他也在其中洞察到对少数一些具有统一性的问题的持续劳作,围绕着这些问题,有关尼采形而上学基本位置的构造地质学逐渐会聚成形。
不过,那种在这里仅仅就其基本特征方面得到勾勒的“争一辩”,其在阐释层面上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同时伴随着另一开端的“对峙位置”;正如我们必须指明的那样,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这个“对峙位置”的意义无疑就在于:在尼采的基本立场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与现代的终结能够被收入眼帘。在这个“对峙位置”领域还包含着这样一回事,即作为对进入另一开端中的追忆的一种本质性“预备”,海德格尔对于关乎自身的“哲学之自我沉思”有所认识(《全集》第66卷,第59页)。这种自我塑造的基本意义(这一基本意义的重要性多半被忽视了)指示着第一开端中的形而上学基本位置的一种永恒特征,即:这种基本位置曾经是(处在其存在意义之中的此在的)“建基”(《全集》)第60卷,第60页)。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