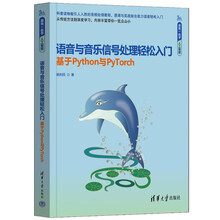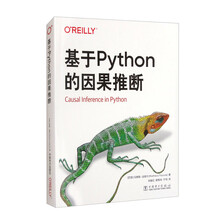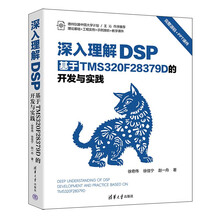溥门记趣/粟庆雄
我可算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又是家中的独子。所以小时在学业上,很受寡母“望子成龙”的万钧压力。在1950年代初,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台北市临沂街六十九巷的一个小弄子里。我正在师大附中念初中,两个姐姐则在“北二女”念高中。当时虽都算是第一流的中学,但母亲对我们的功课督促仍严,还是保留“抽查书包”及“检视课业”之权。有一次母亲抽查我的作文簿,觉得文章不很通顺。她认为年纪已十四五岁了,只会写写“远足游记”或“我的家庭”,而不能做“策论”,真是一种遗感。应当善用课余时间,寻觅良师,补习国文。
有一天,母亲的幺弟,季多舅来访,母亲就以补习国文事商之于他,因季多舅在“世界书局”工作与文学界有很多交往。季多舅便说:诗、书、画三绝的溥心畲,就住在你们这个巷子内,何不求他?只是此人系名士派,不修边幅,终年一袭长袍,发长过耳,满面墨污,家中不用年月,不讲时间,跟他读书,只恐怕小孩子也会学怪了。母亲听了,心中并不很以为然。当时虽未再问下去,却自己去细细地打听。
原来溥心畲先生,本名是溥儒,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是前清恭亲王奕沂之孙。他自幼就笃嗜诗文、书法、绘画,在这些方面皆极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及花卉,与张大干有“南张北溥”之誉,更与黄君璧、张大干以“渡海三家”齐名。书法也是篆、楷、行、草,样样俱佳。文章诗词不但练达、高雅、传神,当时更以敏捷出众,被称为有“击钵之才”。
溥心畲之父载滢为奕沂的次子。溥心畲的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澄,袭了恭亲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畲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畲出生满五个月即蒙赐头品顶戴,四岁习书法。五岁拜见慈禧太后时,从容廷对,获夸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六岁受教,九岁能诗,十二岁能文,被誉为“皇清神童”。后曾留学德国多年,习天文与生物,取得博士学位。1928年应聘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执教,返国后于北平国立艺专担任教席,再度名震丹青,被公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了伪皇帝。溥心畲却严拒伪职,并以一篇著名的文章《臣篇》痛斥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他奉母隐居于北京西山,自号西山逸土。1949年国共内战,为避战火,溥心畲从上海,经舟山群岛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
先母获悉溥先生之道德文章及操守学问,竟然如此超然深厚,心中更觉敬佩,希望早日能将我们送去上课。不久后,有一日傍晚,母亲带了二姐与我外出购物,刚走到巷口,就见到前面有个身材不高,长袍布鞋,发垂过耳的男子,蹒跚而行。母亲一见大喜,两个快步追上,像背台词般高声叫道:“前面走的敢是溥老先生乎?”我们姐弟忍不住发起笑来。但前面的老先生好像很喜欢这种唱戏般的问法,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同时双手抱拳,一揖到地,口中高唱着:“然也。”就这样演戏般,母亲会到了溥心畲老师。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就到溥家造访。落座以后,说明来意。老师很激动地说:国学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在这个“理工第一,英文为先”的社会里,母亲这样的时代女性,能想到为孩子们补习国文,极为明智,极有远见,值得赞扬。他认为,学国学应从“四书”着手,先学《论语》,不但习古文,而且学做人、做事的道理。然后再读《大学》、《中庸》、《孟子》。母亲听了,也深表赞同。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姐弟三人,每周两晚,每晚一小时,来溥家学《论语》,每月束惰新台币三百元。
上课两周后,发现老师教学甚为敷衍,很不认真,精神也不专注。回家禀告母亲,母亲也很纳闷。不久溥老师就托友人传话给母亲说,老师已经知道,母亲是湖南茶陵谭氏之后,母亲的祖父在清朝,曾任陕甘、两广总督,谥号文勤公。当时在台湾,谭氏家族中达官显宦很多。老师特别表示,对文勤公的彪炳勋业至为推崇。但是,既是文勤公之后,何以不明古礼,小孩读书,怎可不行拜师大礼!母亲听了颇觉汗颜,就问友人应如何拜师。他说,溥老很喜欢这三个孩子,也了解我们家境不好,所以不必备礼,去磕头就行了。
下次上课时,我们就补行磕头。老师非常高兴。我们磕头时他并未端坐不动,而是穿起长袍,相对长揖,算是还了半礼。事后,他解释说,这是溥门学生中,受到的最高礼遇。我们是学古文的学生,一般学画的学生就受不到这种礼遇了。
拜师后,老师教学大为改进,不但逐字逐句解释,还引许多旁征。而且规定,每晚上的课,第二次要先背出来,再讲新课。我们姐弟闻言叫苦连天:《论语》的每一小段,在意义上互不关联,背起来非常吃力。
老师非常好客,家中宾客、朋友、学生川流不息,上课时,每有宾客来,他一定特别介绍说:这三姐弟是我的磕过头的学生,他们有出息,是学古文的,不是学画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