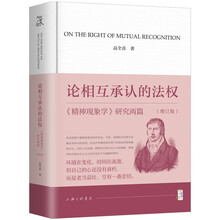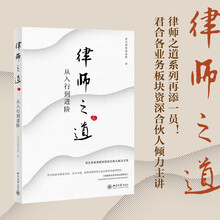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三)关于社会危险性(必要性)条件
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废除社会危险性条件,只要是犯罪,总存在一点毁灭证据、串供、伪证、逃窜的可能,很难断言某一犯罪嫌疑人没有这一可能而予以不捕,在目前的治安形势下,比较稳妥的标准是只要是没有捕错,就是该捕,有逮捕必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故应予以废除”。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逮捕条件中不仅应当规定社会危险性条件,而且要细化这一条件,以增强执法中的可操作性。同时,必须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检察规则》第328条规定,自侦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时应当说明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并附相关证据材料”。这表明逮捕必要性是需要证明的。侦查机关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证据的同时,应当积极收集是否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除提供证明涉嫌犯罪的证据外,必须提供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材料。为了破解社会危险性证明在实践中的难题,江西省检察院于2013年9月建立起审查逮捕社会危险性证明机制,他们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5种“社会危险性”,细化为22种情形,引导侦查机关从法律文书、犯罪嫌疑人供述、同案犯或其他证人证言、有关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方面,收集证据,解决了对社会危险性认识分歧的司法难题。
四、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
基于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通过诉讼程序是实现司法审查的基本途径。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三个基本条件,检察机关只有在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后,才能对逮捕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和决定。而在我国现行审查批捕程序中,只有控方(侦查机关)和承控方(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部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听讼方还没有形成。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克服批捕程序行政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批捕程序还不完全具有“诉讼”的形态。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一般还只是书面审查,并不是必须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更不用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梅利曼教授指出:“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在审查批捕程序中,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逮捕权的制约机制,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
(一)明确审查批捕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辩权有利于改变审查结构上的单向性,有利于形成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诉讼制衡关系,从而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应当明确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是为了核实证据;二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意见,进而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可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三是为了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
(二)赋予被害人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
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将现行的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由审查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另外,赋予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陈述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三)建立批捕公开听证程序
有的同志认为,批捕听证实质上是将批捕程序改造成为一种司法化的审判程序,只不过主持程序的是检察机关的人员,设置一个正式的准审判程序并不能解决批捕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批捕听证缺乏现实合理性。笔者认为,增设批捕听证程序能给予各方充分表达意志的机会,形成各方对逮捕过程的更为有效的参与和监督,实现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的监督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公正、民主的形象。根据批捕程序应当具有诉讼形态的程序要求,批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主体参与,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决的中立机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