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白登之围
此时的刘邦已经亡秦灭项,一统天下,成为秦始皇后第二人,自认为天下英雄无出其右。面对北方传来的匈奴军情,他并不以为然:匈奴只是游寇马匪罢了,当年李牧以赵国偏师、蒙恬率秦军一部都能一战逐之,我若率天下之军,一鼓荡平有何难哉!
这也难怪,出生于南方楚地的刘邦,本来就缺乏对北方胡族的认识,加上一直忙于内战,对匈奴崛起、胡人一统的情势也不甚了解。今年又解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一帮功臣宿将的兵权,他迫切渴望着通过扫平匈奴、收复河套来证明自己的权威。
不久后军报再来:晋阳被围!晋阳是三晋首府,若是失陷,敌人就可以西窥关中,或者南图中原,直接威胁新生帝国的命脉了。
事不宜迟,要把威胁扼杀在萌芽之中。公元前200年冬,刘邦集结全国精锐共计32万大军,亲征匈奴和叛将韩信。
冬天的三晋大地,白雪飘零、朔风凛冽。在刘邦的亲身激励下,汉军顶风冒雪,长途急进,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大败韩信亲率的叛军主力,顺利解除晋阳之围。韩信见势不妙,逃往匈奴求援。老大跑路了,韩信的小弟们只好又拥立赵国王室后裔为王,据守广武(今山西代县)。恰逢冒顿派遣的1万匈奴援军赶到,残兵们士气重燃,再次合军南下攻击晋阳。
刘邦正在晋阳城中休憩,准备过完年就继续北征,直打到匈奴老家去。这一看匈奴人竟然不找自来,他立即挥军出城,以众击寡,大败匈奴于城下。竟敢主动打上门来,刘邦大怒之下,率军追击,一连在离石、宁武等地击破敌军。匈奴人轻骑北奔,向河套方向逃去。
匈奴人果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要不要继续追击,把一场局部的自卫反击战扩大成汉匈全面战争呢?刘邦还是很狡猾的,他派出了多批使者出使匈奴和谈,实则是要探清匈奴虚实。
真是无赖遇浑球,小偷遇贼头。刘邦再无赖再狡猾,也不过是面对项羽的要挟,声言不救老父性命罢了;冒顿那可是装乖卖萌之间手起刀落,直接要了老爹的命啊。相比刘邦,冒顿更加狡猾阴险,他一眼看出刘邦的意图,就拿出以前对付东胡的招数,在汉使面前一味示弱叫屈,装穷认;暗地里却集结倾国之军40万,潜行到了汉匈边境。
听了汉使关于匈奴软弱可欺的报告,刘邦终于下了大战决心。有一个叫刘敬的使者觉得匈奴人是在故意示弱,劝刘邦不要上当,还被关进了牢房。这里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许多人以为刘邦只会用人和耍流氓,在军事方面是常败将军。但实际上,在秦末群雄中,只要不遇上项羽,刘邦可称得上常胜将军。这一点上,刘备继承了他祖宗刘邦的命运,刘备也是谁都不怕,却偏偏总遇上克星曹操,才落得个“逃跑皇叔”的千古误解。
如今项羽已死,刘邦百无禁忌。他一时兴起,竟然自己做了前锋,带着樊哙、陈平等人和数万轻骑,远进到了边境附近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把步兵主力给远远抛在了后面。
站在平城的城头上,刘邦极目远眺,只见飘飘雪花之中,山川辽阔、天地缥缈,好一派北国风光。穿越迷蒙的风雪,他似乎已看到了匈奴人的王庭——等着吧,我要去那里,扫荡那里,征服那里!成为比秦始皇更伟大的皇帝!可惜他不知道,迷蒙的风雪之后不是遥远的匈奴王庭,而是近在咫尺的匈奴大军。
在平城待了些时日,后续主力仍未赶到,刘邦耐不住性子,又率军起程。这次他没能再长驱直入了:在平城以北的白登山,他被40万匈奴骑兵重重包围!史书记载,倾巢而出的匈奴军容极其盛大:白登山的西面全是骑白马的骑手,东面全是青色的马,北面皆是黑色之马,而南面又换成了赤黄色的马。兵强马壮的匈奴骑兵汇成了咆哮奔涌的沧浪之海,而白登山成了大海之中的孤独礁石。
沧浪与礁石,在历史的这一刻剧烈地碰撞冲刷,把命运之弦拨出了震撼人心的高亢之音:如果冒顿全胜而刘邦覆灭,初生之西汉必然崩溃,春秋以来数百年的乱局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匈奴人则有可能成为第一支入主中原的胡人。如此一来,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文明进程将发生不可想象的逆转。
在白登的重围里,刘邦一定曾想起两年前的垓下之围,他采纳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率数10万诸侯联军困住了英雄一世的楚霸王项羽。人生如梦幻,历史竟重演。只是这次垓下换成了白登,项羽换成了自己。难道一生功业就要付诸东流?自己也会和项羽一样,变成后世的笑柄?
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刘邦可能缺乏很多东西,比如家庭背景、军事天才,甚至道德品质。但他最不缺的就是屡败屡战、死不认输的劲头儿。死不认输的人,往往就是死不了的人。生死一线间,刘邦奋起了。他的麾下老兵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凭借白登高地以寡敌众,血战七日七夜。《汉书》就此感慨道:“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弓弩将尽,以山石击之;刀锋卷刃,则斩木接敌;食粮不继,以雪水充饥。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上,汉军将士以一当十,如礁石屹立,把骑兵之海硬生生地挡住了。
七天七夜之后,匈奴人还是无法攻占白登山,攻击的怒潮也渐渐消退。恰在此时,陈平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密计,令冒顿撤除了包围。这个计策的内容是千古之谜,《史记》记载:“其计秘,世莫得闻”。
到了东汉,有个叫桓谭的学者猜测说,陈平的秘计无非是利用女人的嫉妒心,忽悠冒顿的老婆说若匈奴获胜,汉地美女就会全归了冒顿,到那时夫人就会失宠云云。冒顿的老婆忧虑之下连哭带劝,就逼得冒顿退兵撤围了。这一猜测后来竟流传愈广,几乎成了公论,其实是非常可笑的:篡位之前,冒顿为了把部下训练成唯命是从的木头人,亲自下令向老婆射箭;继位之后,为了麻痹东胡,他又把老婆送给了东胡酋长。这样一个极端大男子主义者,怎么可能是听枕边风的“气管炎”呢?
笔者认为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刘邦在白登山坚守七日七夜,让冒顿意识到了汉军的强大战斗力。其实匈奴人虽然长于骑射,但攻坚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以至于后来武帝时候,李陵仅率五千步兵就能扛住匈奴十万骑兵的围攻。要等到发明马镫之后,游牧民发展出了能够冲锋的重装骑兵,才开始对步兵集群占有优势。由于刘邦占据高地优势,弓弩武器的装备又精良,冒顿的强攻始终难以奏效,只有继续包围、困死汉军这条路。
然而,经过这些时日的拖延,汉军的大部队应该已经接近平城了。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冒顿就会面临被汉军主力反包围,从而腹背受敌的困境。虽然胜负未可知,但一场百万人规模的空前血战是免不了的,匈奴即使获胜,也必将国力大损。此时,东胡、楼烦等族刚刚臣服,和月氏的战斗还在继续,统一游牧民的大业远未完成,冒顿可不愿冒这个险。趁冒顿进退维谷之间,陈平之计应该就是晓以利害,以求和解,而冒顿趁机借坡下驴。
当然,才统一中国两年的刘邦也和冒顿同病相怜,而且处境更加危险。冒顿虽然吃不下白登这根硬骨头,但要让他吐出来,还是得换上几块肥肉。所以陈平的计策也必然包含了“和亲、赔款”的妥协内容。后世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辽国萧太后亲自率军大举入侵北宋,一直打到黄河南岸,宋真宗也亲征拒敌。两军对峙激战,谁也无法获胜,最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北宋虽然每年得向辽国送钱,但买到了百年和平。
七日攻势之后,匈奴军声明接受和议,还把四面包围撤除了一面,供汉军撤退。但谁也不敢确认,这是否是冒顿用“围三缺一”的兵法计谋,要趁汉军撤退半道歼之。所以刘邦继续等待时机。
刘邦的坚持终于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史载这天,浓雾突然弥漫了原野,几步之外就不见人影。刘邦抓住时机,指挥全军张弓搭箭、戈矛向外,组成全副戒备的战斗队形,“徐行出围”。匈奴人见汉军阵形整肃,并无溃散之象,也就不敢在大雾天气下出击。经过步步惊心的撤退之路,刘邦终于退回平城,与主力部队会合。
随后他留下樊哙守卫代北边地,并勇敢地承认错误,把当初进谏的刘敬封为关内侯。无论如何,这场艰险无比的白登之围终于落幕了。当刘邦踏上回军长安的归程时,他回首遥望白登的方向,耳边似乎还激荡着那七天七夜的血海涛声,眼前似乎还屹立着如礁石般浴血死难的将士身影。此时此刻,他心中没有死里逃生的解脱感,却充溢着沉重的叹息:虽然安全脱身,但这仗终归是败了。不但收复河套的梦想成空,还要被迫给匈奴献上宗室女子和锦绣财富,从此背负起沉重的羞辱。甚至到一百年后,他的后人汉武帝还念叨着:“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在他心中,一统天下的豪情已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然而,英雄会迟暮,却永不谢幕。正如海边的礁石,在沧浪之水的冲刷下变得黯淡,但细细体味,却别有一种恒久的光泽,黝黑幽深,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在礁石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曾迎风破浪的豪情,也看到了风暴鞭笞的伤痕,更能看到那些比荣耀或者危机都更长久的东西——历史的教训。
刘邦获得的教训是深刻的。经此一战,汉朝终于意识到,胡人已今非昔比,一盘散沙的游牧民族已凝聚成大一统的匈奴帝国。从此,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紧紧压迫着,也激励着刘邦和他的子孙们励精图治、奋发图强。
白登之围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平定九江王英布的叛乱后,路经故乡大宴乡亲,在酒宴上自创自唱了著名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史载刘邦慷慨高歌之时,忍不住“泣下数行”。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寄托了对白登之战的无限感怀吧!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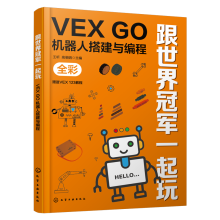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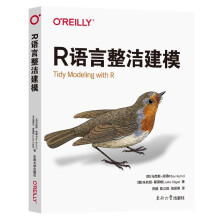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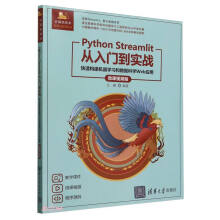


——傅乐成
★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