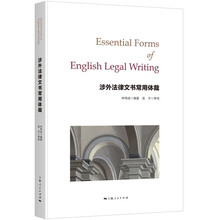不可否认,正当防卫通常存在限度条件,例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权行使的“必要限度”条件,对暴力性犯罪防卫限度的最大化(无限防卫权)是人身法益的最高位阶性决定的,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正方防卫的限度要件。在此意义上,“不法”的程度是正当防卫限度的边界。如侵害生命法益的不法程度明显高于侵害财产法益的不法程度,与此相适应,对侵害生命法益的防卫限度要小于侵害财产法益的防卫限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正当防卫权行使过程中无端附加回避义务,其根源并不出自“不法”的程度所导致的防卫限度,即回避义务自始与防卫限度无关。据此,不能将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中的“必要限度”扩张解释为:不仅包括防卫的限度大小问题,也包括有无防卫的必要问题。毋庸置疑,法律应当对造成了“不法侵害”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进行必要的保护,但不是以牺牲合法权益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实际上,在明知“不法侵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时,统计数据显示除非针对暴力性侵害,否则鲜有行为人对其大动干戈的。因此,在既有的正当防卫条文框架下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不以履行回避义务为必要。如果一定要特别强调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保护而附加回避义务,那么唯有修法一途,即在第二十条中增加相关内容:如果明知是无责任能力人,那么防卫权的行使应以履行必要的回避义务为前提。
据此,就何强等互殴案而言,如果仅仅依据何强等人事先有效地预见了他人可能发动攻击,既未报警也未躲避,而是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召集数人准备工具,就断然否定该案成立正当防卫似乎未免武断,即采取急迫性欠缺说不合理。其不合理的根源恰恰是在正当防卫的判断过程中不当地附加了履行回避义务的要件。换而言之,针对正当防卫前提要件的“不法”作客观的违法性论判断就已经充分,在本案中曾勇等因多次索要赌债不遂而率众持刀前往忠发公司进行斗殴,曾勇等人主观上斗殴的故意不是判断作为起因条件的“不法侵害”时要考虑的,曾勇纠集众人持刀赶至忠发公司,何强等人通过监控看到该情形时①“不法侵害”要件就已齐备;同样的,以何强等人未报警也未躲避而是准备工具为由,否定何强等人行为可能成立的正当防卫,是不当地附加了回避义务的论调,属于不当的过剩评价。实际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也强调:一方有斗殴故意,纠集三人以上进行斗殴,另一方一开始没有斗殴的故意,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斗殴故意并纠集多人进行斗殴的,应注意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的界限。可见,这预留了互殴行为成立正当防卫的余地。此外,域外的审判实践也一改早期一旦预期到侵害就否定正当防卫成立的立场,①而是进一步认为:“正当防卫的宗旨并不在于,对已经预期到的侵害,科以应当回避的义务。”②事实上,审判中这恰恰是争论的一大焦点。
至于附条件的违法招致侵害说,因该说并未摆脱客观说所导致的主客观在体系上的周延性问题,尤其是如果对涉挑衅的行为采取客观的判断,进而否定正当防卫(实际上有时还包括紧急避险)的成立,那么很难解释通说所坚持的偶然防卫成立犯罪(采防卫意思必要说),更不要说成立犯罪未遂了。同时,侵害与违法招致行为存在场所、时间上的密切关联性,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实践中很难把握,这使得采取作为客观说的附条件的违法招致侵害说所导致的结果与对客观说的“精确化”期待相背离。在何强等互殴一案中,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论焦点在客观上大体是“不法侵害”是否存在,而不在于这一侵害与违法招致行为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把握隶属于主观方面,即是否存在防卫意思。
应当说,最终何强等人互殴一案论以犯罪而不成立正当防卫,是通过彼此欠缺防卫意思来解决了,这维持了“不法”与“违法”例外与原则的关系,也贯彻了主客观相统一原理,尽管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不法”与“违法”的关系依旧存在探讨的余地,但就该案例来说很难说不妥当。不可否认,何强等人的反击在形式上并不缺乏防卫的属性,即曾勇等人的举动引发了“不法侵害”的存在,如果采取防卫意思不要说,那么并非没有正当防卫成立的余地。然而,何强等人之所以不成立正当防卫,恰恰是因为防卫意思要件的欠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