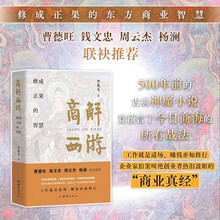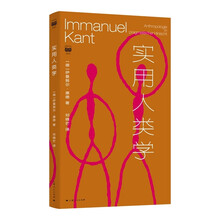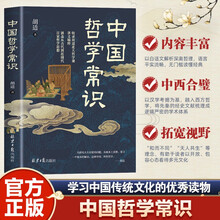如果假定纯粹理性包含有足以决定意志的实践根据,那么实践法则是存在的。否则,所有的实践原理仅仅是一些准则。在理性存在者受本能所影响的意志中,这些准则与被其所认知的实践法则相冲突。例如,某人可以将有仇必报作为他的准则,同时他会明白,这也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准则,而非一条实践法则,因为如果它是适用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法则,那么它将不能与自身相一致。
在自然科学中,事物所呈现的原则(例如,在传递运动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原则)同时就是自然的法则,因为理性的应用在那里是理论性的,为客体的本性所决定。在实践哲学中,即仅仅与意志的决定根据相关的哲学中,人为自身所确立的原则并非是无情限定他的法则,因为实践领域中的理性与主体,特别是主体的欲求能力相关联,而欲求能力的特定性质会导致规则的多样性。这一实践规则总是理性的产物,因为它将行为指定为达致其所期许的某一结果的手段。但是,对于不以理性为意志的唯一决定根据的存在者而言,这一规则即是命令。表达行为之客观强制性的“应当”是这一规则的特征,而这就意味着,只要理性完全决定意志,那么行为将毫无例外地按照规则产生。
因此,命令是客观有效的,并与作为主观原则的准则截然不同。命令,或者仅就理性存在者的结果或者其实现这一结果的充分性而言,来决定其作为现实化原因的因果性条件,或者它们仅仅决定意志,而不管其对于结果而言是否充分。前者是假言命令,仅包含技术性的规则;与之相反,后者是直言命令和唯一的实践法则。因此,准则确实是原则,但它们绝非命令。然而,命令自身如果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决定按意志本身决定意志,而是根据需要的结果决定意志,那么它们是假言命令,而假言命令仅为实践规范而非法则。法则完全将意志作为意志来决定,而不待我问,我是否有能力实现一个所渴望的结果,或者实现它我需要做些什么。因此,法则肯定是直言命令,否则的话,就不成其为法则,因为它们缺少成为实践所需的必然性,完全独立于那些病态的条件、仅是偶然与意志相关联的条件。
譬如,告诉某人,他在年轻时代应当勤劳节俭以免老来困苦。这是一个正确而又重要的意志的实践规范。但是,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出,意志在这里被指向了某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被预先假定为此人所欲求的;并且,关于这一欲求,当下述条件之一成立时,我们必须把它托付给行为者本人做决定,即:或者他预见除自己创造的财富外还有其他财源,或者他根本不希望活到老,或者他认为万一出现困苦的情况,他也能够应付。唯一能够产生具有必然性之规则的理性,亦赋予这一规范成为命令所不可缺少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仅依靠主观的条件,而且我们不能假定它以同等的程度存在于一切主体中。但是,就理性立法而言,所要求的就是:理性需要只以它自身为先决条件,因为规则只有当不关涉任何在理性存在者之间造成区别的偶的主观性条件而仍旧成立时,它才是客观的,普遍有效的。
现在,告诉一个人他不应做出欺骗性的承诺;这一规则仅涉及他的意志,并不考虑他所具有的欲求可否因此而达到。仅有意志为这一规则所完全先天地决定。如果现在这一规则被发现在实践意义上是正确的,那么它作为一条直言命令,可被称为法则。于是,实践法则仅仅关涉意志,并不顾及由其因果关系可成就些什么,并且人们可以通过漠视这一因果关系(因其属于感性世界)以纯粹地拥有法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