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涉及勃洛克的任何一位朋友,只有他的一个朋友(从前也是我的朋友)--鲍利斯·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是个例外。他是无法回避的。
他还活着。对我来说,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他似乎早就死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谈论的是死者还是活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真话。同时,谈论死者又跟谈论活人一样,谁都无法说出整个事实的真相。对有些事情需要保持缄默,无论好事还是坏事。
若要专门写安德列·别雷,我甚至不会有丝毫的兴趣。我之所以要提及从前的鲍利亚·布加耶夫,只不过是因为我与勃洛克交往的历史要求这样。
很难想象还有哪两个人比鲍利亚·布加耶夫和勃洛克反差更为强烈。他们的差别太明显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内在的相似,联系他们俩的纽带,并不十分容易把握和判断。
我是大约在认识勃洛克的同时认识鲍利亚·布加耶夫的(勃洛克大概也是那时认识他的)。虽然布加耶夫住在我们不常去的莫斯科,而勃洛克住在彼得堡,但我们同前者的关系表面上看要更亲近些,不知是友好呢,还是亲昵。
我是在勃洛克的圈子里谈论布加耶夫的,所以我不能停留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仅仅指出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称呼布加耶夫,除了叫他“鲍利亚”,我很难再找到别的称呼,而称呼勃洛克则不同,我是绝不会想到要叫他“萨沙”的。
勃洛克严肃认真,特别好静少动,而别雷虚与委蛇,始终手舞足蹈。勃洛克讲话吃力,少言寡语,嗓音喑哑,而别雷口若悬河,挥臂劈手,表情丰富。他忽而面带微笑,忽而挤眉弄眼。如果你向勃洛克提问,他会半天不吭声。然后说“是”,或者“不”。鲍利亚有问必答:“是是是……”马上会有一千句话脱口而出,腾云驾雾。勃洛克浑身僵硬,就像木头或石头。鲍利亚浑身柔软、温存、甜蜜。勃洛克的头发是深色的、松软的,却不很熨帖。鲍利亚的头发比羽毛还轻盈,黄色的,像刚孵出的鸡雏。
这是外表。说得再稍微深一些。勃洛克--这一点朋友和敌人都感觉到了--非同寻常地,绝无仅有地真实。或许,他也对人撤过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整个身心都是真实的,可以说,他浑身散发着真实的气息。(好像,有一次我甚至跟他谈起这一点。)有可能,他的不善言辞部分地就是起因于这天生的真实。要知道,我想,勃洛克一直抱有这样的意识或感觉(对谈话者来说这很明显):他什么都不明白。他是视而能见的,一切对他来说,他对一切来说,都是言而未尽、含混不清的。很难表达这种痛苦的感觉。他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不明白的恰是那些不明白它就等于什么都不明白的东西。
当勃洛克的这种经常状态表现得特别明显时,我不由地想:万一所有的人同样“什么都不明白”,并且,勃洛克的罕见之处就在于他总能感觉到他“什么都不明白”,而所有其他人却感觉不到呢?
无论如何,对鲍利亚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的实在太多,实在太清楚、太独特、太深刻、太有趣,有时简直是太精彩。无论什么,他岂止是明白,他简直是明白过头了。我说这话时绝对是严肃认真的。我并不否认《话语》--从前的刊名似乎是《白箭》--上的一篇随笔是出自我手。布加耶夫不是天才,也不可能成为天才,而只是有些天才的火花在他身上闪亮,一些不知从何处飞来又飞向何处的天才之箭不时射中他。但他永远都是它们的被动的对象。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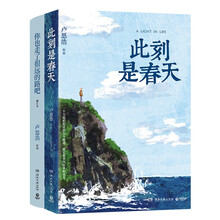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勃留索夫
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回忆录,它同时也是一本精彩的人物画册。在这部回忆录里,作者无意于直接再现事件,她要着力刻画的是个一性——鲜明的、独一地二的,同时义反映了时代特征和趋势韵个性。
——郑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