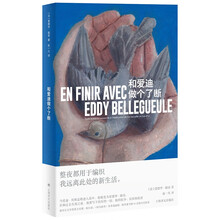一天,安娜贝尔在天空中同时看见了太阳和月亮。这景象让她魂飞魄散。恐惧耗尽了她,直到那一晚以灾难结束时才放手。面临含混,她毫无自卫的本能。
那时她正穿过公园往家走。她用通感解释身边的世界。在此体系中,这公园尤为重要,她爱在灰黄的冬日之光下,沿杂草丛生的小路走,略带紧张的快感。这时节,树秃了,日落时,冷火环绕树枝。某位十八世纪的园艺师将公园种植在一座宅邸周围。宅邸早已被拆毁,一度和谐的人造荒野,如今被时间随机地打乱,绿色缠结洒满小山的高肩。离穿越城市港区的繁忙公路仅一箭之遥。前宅邸仅有的残骸是几件建筑上的辅料,如今已归城市博物馆所有。有一座马房造在那微型帕台农神庙①的边缘,仿佛只为慧驷②而建;那些柱状的门廊,在满月的光线下尤其有效,任谁也踏不进。它不过是一件纯粹的设计品,小山南侧绿色构图中的一个焦点。安娜贝尔很少走那儿,宁静使她厌烦,公园这部分地中海似的样貌提不起她的兴趣。她更喜欢哥特式的北侧,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大格的尖顶拱窗潜伏在树丛中。怕文物破坏者掠夺,这两座异想天开的可爱建筑都被安全地锁好。它们的存在仍扮演最初的角色——公园变成一座预谋好的剧场,在典雅和谐又晦涩古怪的环境中,罗曼蒂克的想象可上演任意一出表演。公园稀有的寂静放大了它的奇异古怪。足球轻落于长草问,零星的鸟儿在啼唱。在这散漫骚动的城市中,无论怎样捂住噪音,都给这鬼祟无风的安静,添了一分不自然。
公园单单保留了一个人口,叫人过目不忘。一对大而重的锻铁门,装饰着小天使,兽面,风格化了的爬虫,和镀金剥落的矛头。两扇门从不打开或关闭,总微微半开,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门枢上缓慢下沉;它们已失去作用,公园周围的所有栏杆早已不知去向,从任何一处进入都简单无偿。处在这样的高地之上,公园仿佛悬在空气中,下面是一块辽阔而多雾的城市模型,那些穿越它的人总感觉过多地暴露于天气。有时,一切看上去不过是一块为风准备的操场,另一些时候,是一条巨大的排水沟,为天空能倒下的所有雨水。
安娜贝尔穿越公园是在多风且气候骇人的季节,一个冬日傍晚。她恰好抬头看了天空。
右侧,太阳照耀着一排月牙形房屋,正是她住的那块区域,同时,在她左侧,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和教堂尖顶之上,渐渐升起的月亮,静挂在一牙儿纯夜的裂口中。尽管一个在降落另一个在升起,太阳和月亮发出同样的光辉,天空同一时刻容纳了两种极端。安娜贝尔向上惊骇地凝望,目睹这对常态的可怕反叛。她找不出一则神话替自己解围,突然感觉是整个宇宙无助的中心点,仿佛太阳,月亮,星星和空中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她——这无意志力的轴心,旋转。
就这样,穿过长草冲出小路,找寻遮掩以躲避天空。她身不由己,蹒跚地呈之字形前进,移动飘忽不定,分明任由狂风怒号随意摆布;她光怪陆离,被逐渐逼近的尘土模糊,不过是那地方、那时节的散发物而已。
小山顶上,她狂躁地挥动双手,用投降的姿态,将自己向小路的一侧倾倒,掩埋在一丛金雀花下,躺着呻吟喘息了一会儿。风将她的发缕缠上金雀花尖,该和预想的那样,纹丝不动才好,直到那可怕含混的时刻,完全溶解在夜晚中。她逗留着,一个疯女孩,沉醉在恐惧中,倚着一丛荆棘林颤抖,痛不欲生,每当挨紧她年轻丈夫白皙的肉体,这痛苦也会袭来。睡在她身边,却不知她的梦魇,尽管他是个美丽的男孩,人见人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