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猎狼者之死 我最后一次见到劳伦·夏麦是在司各特的店里,那时他肩上扛着一头死 狼。我去买缝衣针,他则是去领赏。司各特上过一个美国佬的当,如今坚持 一定要全尸才发赏金。之前那个美国佬,先是带了对耳朵来,领走一笔钱,过一段时间又拿来一对脚掌,再领走一笔钱,最后连尾巴也没浪费。当时是 冬天,他每次拿来的肢体看起来都相当新鲜,这种诈骗的伎俩被大家如法炮 制,司各特很反感。一进门,我就看到死狼的脸,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司 各特喝了一声,夏麦连声道歉。我倒是想气也气不出来,一方面因为他还蛮 迷人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跛脚。狼尸被移到店家后头某个地方去了,我 在店里找着要买的东西,听到他们吵了起来,起因是挂在店外那块长霉的兽 皮。我想是因为夏麦开玩笑要司各特换块新的。兽皮下方有一块招牌,写着:灰狼(性别:公),第一只于考菲尔镇被捕的狼,1860年2月11日。这块 招牌告诉你许多关于约翰·司各特这个人的事。它显示出他的假好学与妄自 尊大,还有为了树立权威而泯灭事实真相的天性。我是说,那只狼肯定不是 这附近第一只被捕获的,而且严格说来,考菲尔镇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镇,虽 然司各特希望它是,因为如此一来就会有个议会,镇长便非他莫属了。“不管怎么看,那都是头母狼。公狼的颈毛颜色深些,体型也比较大。这只太小了。”夏麦不是胡说八道的,他抓到过的狼比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都多。他说 这话时面带微笑,表示他并没有恶意,但是司各特把这些话当成挑衅,并勃 然大怒。“我想这事你一定记得比我清楚,夏麦先生?”夏麦耸耸肩,没有回话。因为1860年时他并不在这里,也因为他是个法 国人,他在我们的地盘上待人处世得小心点。我走到柜台前面:“我想它是头母狼,司各特先生。我记得很清楚,那 个把狼带来的人说,她的小狼哭嚎了一整晚。”司各特把狼头下脚上地倒吊在店外头,让每个经过的人目瞪口呆。我从 来没有看过狼,它的体型之小让我蛮惊讶的。它就那样倒吊着,鼻子直直对 着地面,好像觉得自己很丢脸似的紧闭着眼睛。男人们嘲笑这具尸体,孩子 们则在旁边嬉闹,比看谁有胆子把小手伸进狼嘴里。他们在它旁边摆姿势,闹来闹去的。司各特宝蓝色的小眼睛转到我身上,鄙夷的眼神如果不是在责怪我多管 闲事,就是单纯的不屑,很难分辨是哪一种。“暂且看看他出了什么事。”他说的是韦德医生,也就是把母狼尸体带 来领赏的人。韦德在来年春天溺毙。司各特仿佛认为,提起那件事就能动摇 夏麦的立场。“啊,这个嘛……”夏麦耸耸肩,再朝我眨眨眼。真是脸皮够厚。不知为何我们又聊到那两个可怜的女孩儿,我想是司各特先提的,每次 只要一谈到狼这个话题,人们就不免要聊起她们。虽然世上有不少不幸的女 孩子(我就看过很多),但在这里,“可怜的女孩”指的永远是那两位,就 是失踪了好些年的赛顿姐妹。我们交换了许多不着边际但还蛮有趣的意见,直到门上的铃铛响起,诺克斯太太进门,大家霎时间鸦雀无声。我们假装对 柜台上的纽扣兴趣盎然。夏麦拿了他的赏金,向我和诺克斯太太鞠了个躬就 走了。他离开之后,门上的铃铛还叮叮当当晃了好久。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经过就是这样,没什么特别。劳伦·夏麦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即使如此,我们对他的人生仍然一无 所知。我常想,他跛着脚要怎么猎狼?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用涂了士的宁的 鹿肉作饵,技巧在于要沿着足迹找到最后倒地的动物尸体。我不知道,在我 看来,这算不上打猎。我知道狼群已经学会离步枪远一点,所以它们不是完 全没脑袋,但是它们又学不会别去上免费食物的当。跟着一头垂死动物一直 跟到死,这种方法又好在哪里?他还有其他不寻常之处,比如远离不知名的 家乡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会有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陌生人来拜访他;他偶 尔显露出来的慷慨大方让人目瞪口呆;他住的破旧小屋和他的慷慨形成强烈 对比。我们知道他来自魁北克。我们知道他是天主教徒,虽然他不常上教堂 或者找神甫告解(他长时间不在家,也许他出门这段时间两件事都会做也说 不定)。他彬彬有礼,笑口常开,只是没有特别和什么朋友来往,而且与人 保持一定距离。还有,我敢这么说,他很帅。近乎乌黑的头发和眼睛,脸上 总是给人一种刚刚在微笑,或是正要开始微笑的感觉。他以一种迷人的绅士 风采对待所有的女人,但从不曾冒犯她们或是她们的丈夫。他未婚,看起来 也没有这个打算。不过我注意到有些男人单身一人会快活些,特别是他们的 生活习惯邋里邋遢或不太规律的时候。有些人会随意引来一种完全没有恶意的羡妒。夏麦就是这种人。他懒散,脾气很好,似乎一生顺遂。我想他很幸运,因为他仿佛不必担心那些让我 们烦恼得满头白发的事情。他没有白发,但是他有一段过去,虽然大部分时 候都藏在自己心里。P1-3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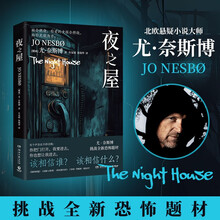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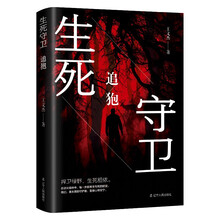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英国《时代》杂志
小说暗藏许多主题,结局尤其深刻!
——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