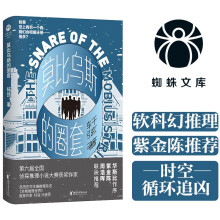菲利浦·拉金(PhilipLarkin)是20世纪杰出的英国诗人、小说家、爵士乐评论家和图书馆馆长。吕爱晶编著的这本《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通过对拉金文论、代表诗作、曾被忽视的经典诗歌、作家的手稿和小说等文本以及同时代诗人对其评价等材料的细读,并联系其生平、社会时代背景、哲学思潮和诗学实践理念,对拉金的“非英雄”思想展开翔实的分析,进行点面结合的描述和阐释,梳理和探究了拉金“非英雄”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诗学与现代价值观。
拉金不是一个冠以过高名誉的小诗人,也不是一个反英雄诗人,而是一位强健的“非英雄”诗人。“非英雄”的概念来源于“英雄”和“反英雄”。围绕“英雄”的问题,历史上的学者在思辨和经验的交界上衍生出诸多的论说。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倡导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普列汉诺夫(Plekhanov)表达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承认英雄历史作用的同时,深入地探讨其“局限性与可能性”;哈罗德·卢宾(HaroldLubin)认为英雄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中所指的英雄具有四个特征:坚定性;神圣性;强权性;超功利性。反英雄(anti-hero)人物形象指地位卑微、名声扫地、行动被动、事业失意或品质不诚实的人物。非英雄是指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普通人物形象。哈罗德·卢宾认为非英雄的行为叛逆、麻木、残忍甚至疯癫。
王进认为他们是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非英雄包括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代表了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拉金作品中的“非英雄”是社会上大多数有工作的、从事“重要”职业、对社会负责任、诚实面对现实的“小人物”,他们不受社会的束缚,不再迷信宗教信仰,是英国二战后长大的零落的一代,是生长在战前战后的断层中的人物。
他们既不是卡莱尔式英雄,也不是英国评论家C.B.考克斯(C.B.Cox)所说的反英雄,是“非英雄”。他们没有传统英雄的神明、先知和伟大,也没有反英雄的游离、执拗和麻木,是诚实的、负责任的英国普通公民(commonman)。“非英雄”是拉金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新类型。它分解了浪漫的“英雄”概念,消解了激越的英雄主义思想;表达了二战后英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特殊情感,体现了鲜明的普通人意识。“非英雄”是日常生活中“完整的人”、“全面的人”,是诗人所创建的“运动派”诗学的精髓。
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英雄的瓦解,大英帝国的坍塌使人们不再寄希望于英雄,“福利国家”彻底摧毁了人们对英雄寄予的幻想。
拉金和他同时代的文人意识到中性是时代的颜色,“非英雄”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境遇赋予了“非英雄”时机,哲学思潮的澎湃铺设了“非英雄”涌现的进阶。实用主义的思潮迫使战后的青年思索自我前行的道路,他们找到了生活中的“实用性”和“当下性”关键字眼。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作家拉金审视生活的视线也转向了生活中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书写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和生存实况。
他以另类的方式寻求异于当时主流的边缘世界,以新的形象去瓦解种种中心价值。这种对中心价值的瓦解迎合了普通人叛逆的心态。
拉金的作品生动鲜明,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关注普通人的思想也契合了19世纪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对人的第二次发现,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进而发现人的“自我”价值。以往的英雄崇拜说到底不是崇拜英雄,而是对“权力”的崇拜,是一种异化。非英雄成了文学关注的主体。从英雄到非英雄,解构神圣,消解崇高,不仅是对人性的呼唤,也是对人性的进一步深化。文学转变为对生命价值的关怀,把文学看作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拉金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文学观的转向,将时代的人学的观念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力图展现出一种新的人的文学。他不写超凡人世的英雄,而关注普通公民的生活,以平等的姿态去体察、去叙述,不作虚假的夸张,淡化以往英雄化、理想化与崇高化,从而无上的英雄神圣性被解构,英雄被“非英雄”取代。读者在拉金艺术的世界体悟自己的现实处境,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共鸣与净化,而不愿在凌空虚蹈的高调中艰难地探索人生的终极价值。
拉金对“非英雄”的叙述是对当时主流英雄文学的叛逆,也是对外来人侵强势文学的一种反叛,同时反映了其“文学自救”的用心。拉金对“非英雄”的着墨,使得其诗歌的历史主体愈发清晰、生动,得以容身于20世纪中叶的文化和权力秩序中,在普遍和特殊的张力中获得更大的阐述弹性。20世纪初,随着美国诗歌的成长和壮大,英国诗歌的本土传统渐渐被美国现代派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学和影响湮灭。这使英国诗人感到耻辱而不断尝试诗歌的变革。于是遂有了A.L.阿尔瓦雷斯(A.L.Alvarez)所说的3次“负面反馈”(negativefeed-backs),一是30年代的奥登,二是40年代托马斯,第三次就是拉金和“运动派”成员。前两次运动没有完全摆脱美国现代主义的影响,而拉金从哈代的诗歌创作中的“小美”思想获取灵感,迅速地从现代派诗歌的重轭中抽身,避开大英雄、大题材、宏伟主题和崇高风格的宏大诗篇,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新视角和可能性,并获得了表达的欣快和写作的源泉,结合传统的格律、鲜活的语言和时代的内容,开创“运动派”,展示了战后英国“非英雄”文学的小美图景。
“非英雄”们通过其平易质朴的语言向世人展现了他们的个性,表达了对世界、对人类自身的看法。纯朴、真挚的口语是“非英雄”的身份证。它清新、自然,与精雕细琢的某些传统诗语截然不同。诗作中的口语词汇鲜明、行文直白、句式结构简单,洋溢着真挚的生活感受。为了增强诗歌的表现力,拉金有时特意避开现代派的那种引经据典、朦胧晦涩的文风,而采用新鲜活泼的“粗话”入诗。“粗话”,在所谓的体面的场合一般是不用的,但它们的出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惊异,如同日常生活的狂欢节瞬间在场似耀眼的璀璨阳光,给新的语言体系带来旺盛的生命力。与现代派朦胧、晦涩的语言相比,平白的口语化语言也是一种诗歌的艺术创新,它的加入给已趋定势化的文学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缩小了诗歌的精神表达与人的生活形态之间的距离,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透彻领悟,呈现了时代的特征。
再者,拉金试图通过诗歌关注自然界被忽视的群体来传达“非英雄”文学的魅力。诗人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个体在平淡、庸常的生活底下的种种隐秘、强烈、复杂、真实的情感,意欲提醒人们对日常漠视群体的关注。
拉金诗中的普通动物或茁壮成长、或痛苦挣扎,从多难的幼年到受难的成年和忧郁的暮年,如尘世中凡人的一生。这类动物是人们自身的文学写照,是“非英雄”的影子:他们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等感性体验和生命体验的真实的、鲜活的普通人。这些“非英雄”人物在有限的生活圈里顽强成长,谱写了人间一首首美妙的“小美”人生交响曲。拉金有意避开现代派专注的大叙事,以普通动物意象入诗,铺叙普通人“非英雄”的故事,也是其“文学自救”的一种策略和技巧。
二战后,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发展,长期被社会忽视的女性迅速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拉金用诗歌的形式展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非英雄”的内在心灵世界。于是,女性内在心灵的律动、潜意识的冲突、生命之流的咆哮进入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主流文学对人的单向关注、机械反映的范式。拉金力求透过生活现象抓住本质,展示人性的深度,反映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拉金审视生活的视线转向了生活中普通女性“非英雄”的现实处境,书写普通人的生存实况。这样的作品回归平凡的生活,揭示生命的本真,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吸引力和亲和力。而拉金的诗作不再是平面化、单一化、直线化的展开,是立体化、复杂化、曲折化的展示,深刻性、复杂性成了诗人创作的诉求。
拉金通过作品关注自然界被忽视的群体,传达新的人的文学,铺展其“非英雄文学”。这样,拉金以其新颖的文学观念和美学风格带动了英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促进了英国诗歌的历史转型,“运动派”由此屹立于世界诗歌之林。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退避”也是一种反叛的方式,把自身强行从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剥离出来,也就是从自身中清理旧有的意识形态。拉金避开宏大叙事的英雄颂歌,改写“非英雄”的平凡之歌,可以说是一种退避,也是一种成熟,拉金的写作找到了“传统与现在”的调和,使其写作找到了安全而有效的写作途径,使英国诗歌在寻求新的方面找到一条捷径。此外,拉金对战后“现在”的直接书写,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惊人的艺术之处,但战后的英国文学,有一长段时间无力把握英国的生活现实,无力揭示新的生活体验和提供新的现实图景,这可以说是英国人的一大遗憾。因此,当拉金用现在时书写时代生活时,他迅速站在时代文化的前列,用“文学自救”的方式开创了英国诗的新局面,挽救了英国诗被美国诗湮灭的危险。拉金作品中平白语言的实验、日常动物的象征和普通女性内心世界的刻画,又构成了拉金“小美”图景中璀璨的光芒,体现了平凡中的、常态下的崇高和神圣,冲击了人们旧有的审美观。当然,平淡的诗语、“非英雄”的日常故事有时会令读者感到拉金的诗歌过于生活化,淡而乏味。但诗歌若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葆青春,就必须不断地改革更新。世人要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拉金的诗歌,并对诗人的努力创新予以足够的肯定。
总之,拉金的“非英雄”思想映照了战后英国青年一代的精神群像,显示了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摆脱桎梏及思想蝉蜕的过程;传达了时代新的人文关怀。它不仅尊重了人类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规范,而且从艺术上表现了普通人传承的生命活力,记录了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拉金的“非英雄”文学展示了日常生活的美丽,促进了英国诗歌的历史转型;体现了当代文化的主要价值,折射了后现代文化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艺术的关注的新文化景观。它启示人们:在本土与他方、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在变动不居的历史境遇中,挣脱历史的陷阱,构建诗歌的主体。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