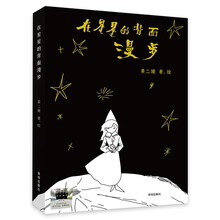卡萨布兰卡,1978年年月27日,返回巴黎前的早晨
哀痛。
在这里,一连两周,我不停地想念妈妈,不停地忍受着她的去世。
到了巴黎,还会有家,还会有秩序--当她在世的时候,这种秩序就是我自己的秩序。
在这里,远不是这样,整个秩序都垮掉了。奇怪的是,当我“在外面”、远离“她”、寻欢作乐(?)、“休闲消遣”的时候,我则忍受更大的痛苦。在人们对我说“你在这儿拥有一切,可以忘却其他”的时候,我却更难以忘却。
哀痛。
妈妈去世之后,我认为:我在仁慈方面有了某种解放,她还经常作为榜样(形象)出现,而我则从引起那么多斤斤计较的(对于顺从的)“惧怕”之中解放出来。[因为,从今以后,我不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吗?置之度外(对于自身)难道不是某种仁慈的条件吗?]
但是,哎,情况却是相反的。我不但没有放弃我的任何自私、任何微不足道的所爱,不但继续不停地“有所偏好”,而且,我还不能把爱投注到某个人身上。所有的人都在我的关切之外,甚至是最亲近的人。我感受到了--这当然是很难受的--“心的荒芜”,即疏忽。
1978年5月77日
昨天晚上,看了一部荒谬和粗俗的电影--《一二二》①。故事发生在我经历过的斯塔维斯基事件②时期。一般说来,这个事件不会使我有任何所想。但是突然,背景中一个细节使我情绪激动:仅仅是一只带褶皱灯罩的灯,它的细绳正在下垂。妈妈过去常做灯罩--因为她做过制作灯罩的蜡防花布。她整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