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九八四年吧!我还在靠全省“走透透”的到处作西餐厅秀为生,同一年认识了从美国学戏剧回来的赖声川,大家一见投缘。
本来,赖声川曾经和兰陵剧坊的金士杰、李国修讨论过一个想法,他觉得“相声”这个文化在台湾好像消失了,或者说“死了”,当时那个十年左右,确实在媒体里,已经极少听得到相声的表演,上一辈精彩的相声演员,去演电影的演电影,开集邮社的开集邮社,到美国移民的移民,其他的相声演员也多半因为生活所迫,为了糊口,能改行也就自然地改行了,所以各种北方相声、南方滑稽、说说唱唱等节目,渐渐地真听不到了,而且有十几年的光景,没了!
我在刚出道的那几年中,二十八岁那年吧!参加一部电影的演出,巧遇了小时候的相声偶像演员,魏龙豪先生。我去跟魏叔打招呼,表示敬爱之意,魏叔也知道我这个新演员,不见外地聊起天来。我当然也像现在有许多人问我一样的问题,我也很关心很期盼地问魏先生:“为什么这些年在收音机里都听不到你们精彩的相声表演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魏先生百感交集的表情……重点就是说,环境不行了,新段子难产,老段子听多了,收入过于微薄,社会地位偏低云云。同时也很感慨地说许多好友也劝过,鼓励过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包括葛小宝先生也曾三番五次地激励过他。但是,他还是不后悔不再讲相声了,所以他们那几位也就各奔东西各自生活去了。
话说当年赖声川与李国修、金士杰在兰陵剧坊相识,合作过,彼此都颇能信任,本来是他们三个人要做一个相声剧,主题是“文化”这个东西,会因为一个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文化”这个东西会自然地悄悄地就跟我们说再见了,“文建会”也好,“文化部”也好,花再多钱想去复兴它,或者挽留它,也未必有用。这个主题不错,换句话说,他们想用一次“相声剧”的演出,来表示对相声在台湾消失作一个哀悼,就是替相声写一个祭文吧!这就更好玩儿了。
可是金士杰当年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赞助,去美国游学去了,声川和国修就找上了我,一聊,我说好哇!相声我从小就爱听啊!可是爱听不表示就能讲啊!更别提怎么编写怎么创作啦!于是,三个人把当时海峡两岸所有出名的相声演员的录音带,收集了个差不多,开始听,听了又听,记下笔记,讨论,我和声川又去听过一次魏龙豪先生的演讲,谈相声的结构法,最最主要的还是三个人听了很多的录音带,而且还有心、有意地去里面找方法,找为什么。
找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不管是否有三年拜师,五年出师,或者什么“说”、“学”、“逗”、“唱”、“捧”等相声的基本动作一定要纯熟啦等等条件,就凭着赖声川,一个让我们俩信得过的一位舞台创作导演,还有国修编、写、演过电视短剧,我也演过不少短剧和两千场左右的西餐厅秀的经验,再加上我们对相声的热爱,就不论成败,也没什么压力的,便开始替相声写起“祭”文来了。
说起祭文这个意思,让人觉得生命这个东西“生与死”的关系,往往透过某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或者说,一篇有感情的祭文,或者说,重新演义出死与生的关系,或者说,就当他还没死,还在活着。这是种虚中带实,实里又带着几分诡异,然后手法上又是寓传统于现代的,以相声的方式说出来的语言戏剧。在我们三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心态下,该做历史调查的去做历史调查,有感而发就别憋着,每天嘻嘻哈哈地工作到深夜,有的时候愁眉深锁地去设想一个包袱到天明。
由于没人逼着我们硬要做什么,由于票房的压力不存在(那年月舞台剧能演出就不错了,没人去想票房),由于三个人的创作理念接近,也由于三个人都还年轻,我最老,才三十三岁,都还很有闯劲儿,经历里也都有足够的热情,不急不忙,也不浪费时间的,用了半年的时间,删掉了大约四倍的长度,最后变成了我和国修在台上演出的长度。
国修的思想够现代,表演语言非常精准,有我完全没有的一种情绪组合的方法,他在《台北之恋》的段子里述说了一段只有一个钟头的恋爱故事,语气特准、节奏特准(不是一般人的节奏)。在《电视与我》里替我帮腔的表演,更是浑然人里与说者完全合一,我在帮他的《台北之恋》文中,便显得暴躁过多,谛听较少。在那两个段子里,我对国修无形的表现,百听不腻,每每赞赏。
当然,如果没有二十八岁就得到柏克莱戏剧博士的赖声川的旁观、监督、规划,我和国修的表演经验,自创的能力,就不太可能长成如此的形状,我们三个人的幽默感,也未必就能发酵起来,以至于让久违的台湾相声得以复苏吧!
大部分的创作,多半是由逻辑来领导感觉,也有的作品是感觉影响逻辑,我们大概是属于后者,师出无门,自摸自学,勉强算是个“野人献曝”。
大陆近年来的相声创作,也有式微的现象,可能也是过于重视逻辑,不知不觉地埋下了迷失的种子。最近,出现了一位郭德刚先生,表演相声的经历非常丰富,台上的“精、气、神”相当好看,希望他未来能够愈来愈好。
2004年10月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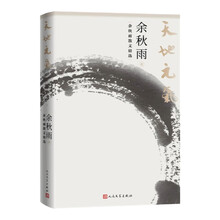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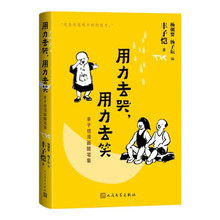



——蔡康永
喜欢李老师对“雄浑”二字的体解,正如其人其戏其文,以大雄之志游戏人生,浑然不露锋芒,令晚生叹服渴仰。
——崔永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