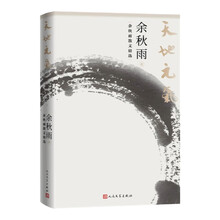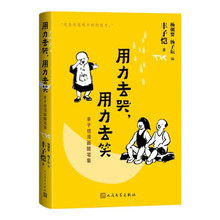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只鸟,对着蓝天,有一种想飞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对世界充满认知的渴望,可那时,翅膀还没有力量,没有足够的经验,长大以后,尝试着飞得更高,可是没多久就飞不动了。等到羽翼丰满,就飞出了巢穴,傍晚时分再飞回来,直到最后不再回来。到那个时候,家已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巢穴了,而是整片天地。
——《白云深处》他过的是一种简单而美好的生活,无挂无滞,孤云出山,来去自由。出身中药世家,八岁母亲过世,十七岁便离开家,从事过许多职业,一路行走,最后徒步走到终南山归隐山林。
作者问他为什么选在这里不走了,他讲:“因缘到了。”有一次山下有人来访,见面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想了半天没有记起,身份和名字在住山的日子里被淡化和遗忘了。如果你问他心里喜欢什么或讨厌什么,他会有一点茫然,因为这个区别似乎已经忘记很久。他叫明居士。
在山里行走时,有时会没事跟着一朵云在山里走,云彩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顺着山路或者草丛会跟着云彩走很远,回来的时候,手上会有新鲜的野菜、蕨菜和蒲公英。蒲公英也是一种野菜,有时他会把鲜嫩的蒲公英的茎叶入食,然后把那些已成熟长大的蒲公英吹散,落花细水,风吹云淡,吃过蒲公英后,或许感觉自己就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在地飞翔了。他喜欢看云,坐在树下,看着云朵从西边的山顶向东方飘去。有时云会飘得很低,会被风吹到屋檐附近,但一转眼,它又变化成另一种陌生的形状。
他说:“看云彩能让你明白世事无常的道理,一切都在变化,不变的只有自己的那颗心。如果杂念与贪念太多,就会心力涣散,就会产生执著。其实时间是可以忘记的,而心里的挂碍也是可以忘记的。
忘记了就消散了,不会再困扰了。”早晨他是一个樵夫,中午是农夫,站在自己开辟的院子里锄草,而到了黄昏,他是一个修行的隐士,没有晚餐,只是喝点水,在屋檐或者树下静坐。一日两餐,有时一餐。他食的很少,有时自己会在石凳上煮茶,剥松子放进瓷碗里,给路过的人招待取食。打坐时,小动物会来看着他,或吃他准备的食物,久而成为朋友。他说:“经常食肉或者大量饮酒的人,走在山里,会引起动物们的警觉,因为欲念过多,气息会被灵性的动物感知,它们会特别警觉,或引起它们的攻击性。人的痛苦总是太多,我们心思褊狭急促,很大原因在于我们接受的信息太多,而不善于恰当地处理或者删除。心受到了太多的无形压力。太多的顾忌和讲究只会是一种拖累,修行就是让一切回到它本来的面目。”“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在这一住便是十年,十年对他来说恍如一瞬,一个念想而已。他的心静极了,心静的时候就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声音。时间是住山者很少追问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幻生幻灭的事物。在山中的日子,明居士有缘结识了一位生活中的伴侣,名叫宽宏。萍水相逢,但是对于世间的事情,并非用偶然能解释的。他喜欢劳作定禅,她喜欢看书打理,有时他们会聊上一整天,或者背着竹篓带一点食物和工具,去山里采药,直到黄昏的时候回来。他们不举行婚礼仪式,也不要孩子,在山里能住多久就住多久,一切随缘,十年来从未争吵。时间对他们来说仿佛仍停留在某处,就像云朵。终南山那么多的云朵,你永远不会知道现在头顶上的那片云是不是你多年前遇到过的。
或许,它兜了一圈,又漂泊于此,你已经不识得它以前的样子了。
他对作者诠释了这样的爱情。他说爱情分三种:“初期叫占有,占有对方的身,心,情感;中期叫放手,只要对方快乐,就可以放开一切,不执著;终期叫绝情无爱,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爱有慈悲。第三种爱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当他们需要占有,需要放手的时候,我们就掌握好时机和因缘去占有或者放手。当然,这里的他们不单指外界之人,也指我们自性中的贪婪、嗔恨、痴迷。我不爱任何人,别人爱不爱我也并不重要,无所谓爱和不爱。只要她快乐,她开心,她幸福,这些所谓的名称,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都不重要。
同样的,我也希望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这样。当对方需要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就放开她。同样的,这也是放开我们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就叫绝情无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