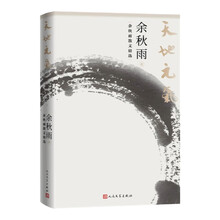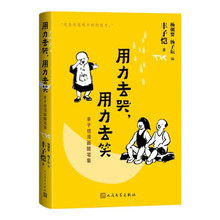园博园至文
——草木有情牵蝴蝶,名花无主寄骚人
戊子年初,粤地春迟,飞绿凝花,飘摇无算。晚阅学生纪游散文《游园博园——悼念我的小姨》竞至跌入此文哀痛,伏案抹泪。这是师范学院应用心理系钟凯旋的文章。本来此作可以下周上交老师,钟同学却是七十四名同学中第一个交来作文的。虽然韩国外国语大学交换生卢妍希送来《游锦绣中华》一文,应用心理系田钰姝送来《园博园游记——浅谈福》一文,但是我就觉得钟同学的至情悼文才是第一个交上来且不负苦心的压卷之作。
且引此文一些文字:
“时间就如此快乐地在我们的指缝中流逝,最后‘小猪’(同游的恋人同学)竟然娇滴滴地说:‘我不高兴走了,你背我……’顶着巨大的痛苦,我竟然背着她从长长的阶梯走到了综合馆。她笑了,笑得很甜很甜,可是我都快哭了……”
“惊醒,仿佛看见穿着白色婚纱的小姨又出现在我身旁:小姨好美……如果不是狠心的小姨夫,小姨的生命会延续么?”
“却从未发现,有神的存在……”
“再次入梦,再次来到园博园,再次看见美丽的新娘……”
“纵身一跃,我拉不住我的小姨……”
以下是我的评语:
我也泪流满面!这是至情好文章,好像有灵魂在催迫写成此文,实际上科学不能证明灵魂为虚,也不能证明灵魂为真,我相信她(小姨)是真的。
这个还未曾谋面的钟凯旋同学带着他的同学情妹在飞红流绿的季节——恰好与他的恋人“小猪”都没有课,硬着头皮答应同学才有园博园一游,没想到以恋人身份去的,最终在园博园里却误将“她的笑脸”当作了小姨的笑脸……
“手牵着手来到公交站牌下,我抬眼望去,红色的木棉花开满一树,终于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下来:小姨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木棉花——看似温暖,内里却充满忧伤。我拾起一片掉落的木棉花瓣,竟放在嘴里咀嚼、吞下,试图让木棉花的生命随着我的生命延续么?”
写到这里,我无法不想起我最近作的几句诗——外表温暖、内里却充满忧伤:
墨竹数支试天风,月在中庭人梦中。
又是岭南春来早,飞绿疑将花飘摇。
春来花发千万支,独有一支自飘零。
我在今春虽然还不至发痴如钟同学般拾起木棉花瓣,咀嚼、吞下,但却因为痛失一位亲戚——连襟兄弟,他的音容笑貌、俊朗神秀时时悻悻于胸。就像钟同学说的:这个春天有着痛的痕迹。人至中年,应该说痛的痕迹越来越多。春天容易生长些什么,也容易凋零些什么。前年我的嫂子、去年陈晓旭、今年我的连襟兄弟,美好的人、美好的笑容转瞬即逝,流水有意,落花无情……岂止是落花。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深大校园五月暮春交夏,荔园西南一带绿荷茵湖、烟雨菡萏。我每天放弃乘车,步行去上课就是为了看荷、赏荷、叹荷。文山湖下出现的这一处绝景曾让一干路人何等的惊艳!可是,这令人欢喜不已的一池绿荷红葩连同悄然出没的翠乌们,自校园的西南角遽然绝迹。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那么大的一片绿荷红花突然就死绝枯灭,全校师生都来不及叹息一声。我想写一篇悼念荷池的文章,却无从下笔。直到5月18日报纸上报道陈晓旭辞世的消息,我才恍然惊觉:原来同病相怜的荷魂花灵都紧随着在附近修佛的当代林妹妹飘然已远?有陈晓旭十四岁时的《柳絮》一诗为证:
我是一朵柳絮,
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
因为父母过早地将我遗弃,
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已。
我是一朵柳絮,
不要问我的家乡在哪里,
愿春风把我吹到天涯海角,
我要给大海的角落带去春的消息。
一切皆缘,你看陈晓旭一语成谶。她从遥远的东北,冰天雪地的,以一朵柳絮的飞落,回归南海绝岛。虽则当代林妹妹溘然长逝的所在地高楼环立、人气鼎盛,但在诗的时空、情的背景下,这深圳依然是“天涯海角”。当年少女陈晓旭以这首《柳絮》短诗博得导演青睐,演出家喻户晓的当代红楼梦一场。斯人已去,斯美仍在。春天凋零了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的生命,使我们无法不想到凄美——一种特殊的美学,其极具传染性,就像它传染给这个同学少年钟凯旋一样,又毫不犹豫地传染给我,让我在例行公事批改学生作文时,泪水模糊了双眼,又让我在久久不能平静之余在学生的文章之后大笔一挥:
小姨薄命哀,外甥情分长。
园博园中景,花谢花飞殇。
吞红惊痴绝,落笔裁华章。
三月本如梦,地老到天荒。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