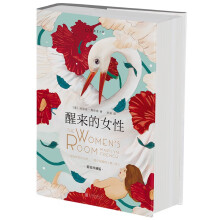上卷 我上的那所大学并不怎么有名,地理位置却是全国高校中 独一无二的。那地方叫银石滩,地处祖国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这实在是一片奇异的海域。海岸地貌呈海蚀阶地状。落潮 时,可以隐隐看到那道贝壳堤,据说是古海岸线的遗迹。海滩 上布满各种形状怪异的砾石。沿着海岸线往西南方向走,便矗 立着那片石林——每根石柱上都布满了软体动物腐蚀的斑点和 穿透的孔痕。这里实际上是个伸进海洋的小小半岛。半岛上那座小小的 城,叫渠州。听说这儿自古以来便是一片动荡不安的海域。这 儿的地质构造运动大概比其他海岸要激烈频繁得多。海陆不断 地变迁和更替。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沿海大陆架就变成了陆 地。海平面一上升,大片陆地又被海水吞噬,于是小小的半岛 与大陆分离。这学校的历史应该算是很悠久了,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爱国 华侨闯了南洋之后集资兴办的,升格为大学却只是不久前的事。那位华侨选择了这样一片海域,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这儿又有许多传说,最盛传的是关于“海火”的故事。据 说,石林的夜晚常有魔鬼出没,而且鬼见到人便附体,于是人 也就变成鬼。孤魂野鬼们平时镇在石下,一俟月黑风高之夜便 纷纷出来游荡。相传那时的海像着了火似的,亮得灼眼,又忽 然化作一片白雪,上面有绿的光,螺旋似的飞快旋开,展示各 种美丽的几何形图案。直到三更天后,普陀寺钟声响过,魔鬼 才归位。如有求签者,于彼时去石林跪香,没有不灵验的。初时听到这些传说,我们不过是觉得可笑。又感叹天高皇 帝远,封建迷信的东西在这小地方仍有这般市场。真恨不得立 即悬张告示,动员附近渔民都来捕鱼。大家商量,一定要找个 机会在石林附近闹个通宵,为当地人做个榜样。校园是美丽极了,真正是依山傍海,海都伸到露天剧场旁 边来了。每天傍晚,这儿都有许多来看落日的。长了,仿佛是 掐准了点儿,就差喊句一二三,落日便在那一瞬间,像只失了 光彩的红色大球,软软地滚落到海平线的那一边。然后就是那 些云,浇了浓杏汁似的,恋恋地在天边翻来翻去,一会儿,也 隐没了,只留下那群巨人般的石林和侏儒般的人对峙。再过一 会儿,终于侏儒们走了,这里就成为巨人们的天下。开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礼堂门口等哥哥。鬼都不 知道他为什么销了那个来之不易的北京户口,非要到这所大学 的图书馆来工作。谁管得了他的事儿!连爸爸妈妈也管不了。我只好缩脖耸肩地瞪着台阶下面那一片片流动的伞,身上一阵 阵发潮发痒,我当时那样儿一定挺傻。伞下众多的脚一步步踏 上石阶,离我越来越近,当近到不能再近的时候,那些伞便纷 纷扬扬地收拢来,露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总会有几滴冰凉的 雨水溅到我身上,这一片伞的颜色还是灰的。那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刚刚准备甩掉“蓝蚁之国”的名讳,所以突然出现的那一 把花绸伞在这许多的伞中显得分外戳眼:浅黄底子,上面绘着 咖啡、黑和西洋红三色图案,远看,像滚滚的灰水里漂过来一 朵鲜艳夺目的花似的。只是那伞打得太低,直到礼堂门前才略 向上抬了抬,露出一张线条精致且白得醒目的脸。这人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她和我在一个 班,名字和肤色一般白,叫小雪。再后来,我明白她的出现给 我带来了一点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一直期待着的那种变化。那 时,我明白我不再期待什么,而我本来的期待也是荒谬可笑的 了。人说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班有八个女孩子,果然热闹非 凡。头一次上政治经济学大课,三个系都挤到大教室,真真是 比肩接踵,连咳嗽放屁都能引起连锁反应。大教室显得挺庄严,玻璃窗太巨大,没安窗帘,阳光便射进来,像一个个明亮的圈 儿,九连环似的飘来飘去,光圈中舞动着无数颗金色的尘粒。小时候我曾以为那就是原子,后来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我 相信那不是原子。让一个孩子相信他看不见的东西很难,却又 很容易。说起来,孩子心里总有点儿什么东西,只不过人一长 大,就忘了。我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是不是非要这样讲法,大概是一定的。因为几位老师,包括今天讲课的权威王教授都是这样讲的。王 教授操闽南口音,话不好懂,又兼牙齿暴,讲起话来难免溅出 些唾液。那一圈圈明亮的光环里的金色粉尘,忽而都下雨似的 沉落。王教授的嘴巴熟练地一张一合,他眼前放着的是用了几 十年的讲稿。当然每逢什么特殊的时候要做些增删,但基本内 容是永恒不变的,因为这是根据《资本论》中的观点写成的,而马克思的话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想,如果这位满脸胡 须的圣者至今活着,对此不知持何态度?我看着王教授蠕动的 嘴巴,硬是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只要有一秒钟的松弛,我眼 睛便乜向那纷纷下落的金色尘埃。终于,王教授拿起粉笔,很 用劲儿地在黑板上写下那个庄严的公式:一只绵羊=两把斧子。于是学生们的头立即沉下去,像一片黑压压的蝗虫,笔尖 在纸上啮咬出沙沙的声音。这课堂真是庄严极了。前面一排人 那齐刷刷的后背,胖瘦高矮全是一个姿势。头微偏,肩略斜,一式地向左看齐。只有我斜前方那个苗条的后背有些特别,她 是笔直坐着,笔直向前倾斜着角度。显然她没有记笔记,而是 在看什么东西。她的背影很有韵味,斜削的肩,柔和的腰部曲 线,乌发像两道墨线似的垂下来,发梢在我邻桌小胖子王妮妮 的铅笔盒上散开,黑羽毛扇似的发出淡淡的幽香。黑发的光波 里闪亮着一对红樱桃似的装饰珠子,色彩对比如幻影般强烈。我想她一定是十分爱整洁,连那两粒珠子都是纤尘不染。什么 东西这么吸引她?我左顾右盼地看了好几眼,什么也没看见。为了显得和大家一样,我强迫自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串莫 名其妙的符号。这时我感到一只胖胖的小手正在掏我的口袋,原来王妮妮一直在偷我衣袋里的瓜子吃。发现我觉察到了,立 即很自觉地把一块巧克力放进我的手心里,以示交换之意。我 们毕竟正在学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呀!我微微一笑,瞟一眼 王教授,他没有朝这边看。我慢慢把巧克力推进嘴里,不料这 块巧克力里面还包着一颗脆生生的果仁,我的嘴里立刻发出一 声清脆的声响,刹那间我呆住了。这一声在我听来不啻炮弹落 地,连耳朵都震得麻麻的,立时感到整个教室的目光都在向我 压来,威严的王教授正慢慢向我逼近。我听天由命地朝上翻翻 眼睛,这才发现谁也没有注意我,只是前面那戴一对红樱桃珠 的女孩子回身瞥了我一眼,随即又低着头嫣然一笑。就这样,我一下子喜欢她了。记得见面会时她自我介绍说叫郗小雪,是 本地的。听她讲一口纯熟的北京话,有人问她籍贯何处,她笑 而不答。她的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不仅能迷男人,还能迷我 这样傻乎乎的姑娘。我又低下头来记笔记,“噗”的一个纸条落在我的活页夹 上,眼明手快的王妮妮一把抓过去,展开一看,便趴在桌上笑 得死去活来。王妮妮的笑特别富于感染力,笑到极致,大家便 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连一向严肃的班长郑轩也像被别人掐住 颈子的公鸭似的,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王妮妮,你笑了整整 五十秒钟,给你掐着表哪!”男同学在后面抗议。纸条上是幅漫画:一个暴牙老头站在讲台上口沫横飞,下 面是满满一屋子打伞的学生。我笑着在上面题字日:“一句话= 一百二十把伞。”正在得意,谁知玩笑开过了头,老头循笑声而 来,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尊容,勃然大怒而去,丢下一屋子呆若 木鸡的学生。前排的袁敏就回过头来了,目光冷冷地扫荡了一番,最后 停留在郑轩脸上。郑轩立即作俯首状。袁敏是全班唯一的女党 员,而郑轩正在争取入党。同学们呆了一会儿,又都哗然,纷 纷离座。袁敏便站起来很严肃地说:“这件事需要追查。”话音 未落,正欲冲出教室的何小桃“哎哟”一声跌落尘埃,原来是 王妮妮趁乱把小桃那漂亮的亚麻色大辫子一圈圈地绑在椅子背 上。王妮妮又笑得背过气去,周围的同学也忍不住笑,唯袁敏 冷着脸一声不吭。我这才注意到,满屋子的人只有郗小雪纹丝 没动,周围的喧嚣像是要把她抬起来似的,她却静坐其中,安 静得像棵植物。P1-5
展开